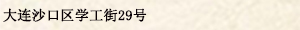文学之窗李本深长篇小说桃花尖3
李本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兰州军区专业创作员。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及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暨鲁迅文学院文学研究生班。著有中篇小说集《西部寓言》、《汗血马哟汗血马》、《昨夜琴声昨夜人》,长篇小说《刀下泪》、《唐林上校》、《海子》、《疯狂的月亮》等多部,。其小说《丰碑》被收入中学课本。中篇小说《神戏》、《吼狮》、《沙漠蜃楼》、《黑树》、长篇《西部大找水》等十多部作品曾获十多种全国和地方文学奖。是年元旦在央视黄金时间热播出的22集电视连续剧《铁色高原》编剧。
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小说。以具有浓郁乡土味的叙述方式,从厚重的历史积淀之中发轫,徐徐展示一幅黄土高原村落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以及两代人不同的命运走向画图。在十分恶劣的生存困境下,在岁月的淘洗中,西部农民熔铸了一种坚忍不拔、从不向命运屈服的黄土精魂、奋力向上的西部人格。通过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交织生活的矛盾和纠葛,展示不同的人生轨迹。成功塑造了以何佛留、狗蹄子、黑女子等为代表的两代西部农民形象,从人性的深处挖掘了当代中国农民在走向现代过程中面对艰难过渡、历史重荷、未来困惑等,所做出唯一的抉择——紧紧跟上时代步伐,将自己新的希望寄托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的目标。黄土大山里的风俗画图、西部独有的地域特色、朴素自然的故事,以及富有艺术个性化的叙述语言,构成了浑然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
…………………………
35、半道儿碰上个贼
那天是虸蛖娘娘的庙会。
狗蹄子起个大早到蚂蚱镇去买硫酸二氢钾。买硫酸二氢钾不过是何佛留老俩口使唤狗蹄子到镇上来的一个借口,他们真心是想让大儿子出来走转走转,发散发散窝在心里的郁闷。从去年秋里到今年春上,老俩口全部心思都转回到了狗蹄子身上,托人给他说过几个女人,多半是新寡。狗蹄子表现得却没啥心思似的。
我父亲说:“发有,这一辈子的光阴还长哩。”
“一个人也过惯了,再成个家,还不就那么回事,不够婆烦的。”狗蹄子嘟囔。
“你是以为那扫帚星还顾念着你哩?”我父亲说的是刘菊儿。
“你再少提她。”狗蹄子顿然烦躁了。他并非不希望再有个家,可他明白,何家再也经不起折腾了,这个家决不能败在他手里。支撑起何家的家业远比讨个女人来要重要。另一方面说,他也真看不上旁的女人。凡事就怕比较,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刘菊儿自不必提了,他眼皮底下不是每天都晃着个一个真实的女人的影子么?这就他的兄弟媳妇。有了桃花做比较,他看不中旁的女人就没一点奇怪了。
他在院子里碰上正准备下地去的桃花,太阳还没出山,山里的岚气很重,空气清新得像用清水洗过了似的。
桃花说:“发有,走集上去呀?”
“噢。”狗蹄子停住脚:“桃花?你有啥要捎带的没?”
“可没。”桃花淡淡地一笑。
狗蹄子忽然发现桃花似比早初憔悴了许多,就像棵久旱的青苗呢。她在抬头瞅他的那一瞬间,前额上居然隐约现出几道细微的皱纹,像新鲜的蛛丝。虽然这隐隐的皱纹瞬间就从她额头上消失了,但他的心还是为之一颤。
“你有啥事可就言喘啊。”他望着堆满豆秧的场院,声音有些含混。顺手背上背斗。
桃花叫住了他:“发有,要不了……”
他回头望着她的眼睛:“啥事你说。”
“其实也没啥要经的事。”她勾头望着扫得光净的地面上刚落下的几瓣桃花瓣儿,那桃花瓣儿“像落在地上的,倒像用鲜艳的颜料画在地上似的:“今天不正好是虸蛖娘娘的庙会吗?还说去给虸蛖娘娘进个香哩,你去了正好捎带着替我上个香吧。”
“就这事?成。再还有啥?”他答应得很爽快,而且情愿。
“就这,可甭耽误你浪集。”
“两不耽误。”狗蹄子心里暖暖的:“光烧柱香?许个啥愿哩不?想许啥愿你就说。”
桃花移了目光,轻叹一声:“这倒把人难住了……”
狗蹄子转念一想,笑了笑:“不说也罢,你自家心里得想着,那愿才灵验。”
“嗯,我就在心里想着。”她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期待和渴望。
狗蹄子虽木讷于言语,却绝非傻汉,如何能看不出她眼里的东西?
虸蛖娘娘庙是座小庙,周围几棵古柏。我们小时候常去庙里玩耍。那时的庙十分破败。香火盛起来也就这几年间的事。
传说明朝洪武年间,胭脂山里闹蝗虫,遮天蔽日的蝗虫乌云般扑来,不仅吃光了地里的庄稼,连大牲口身上的畜毛也啃吃一光。幸亏一位邋里邋遢的肖道士,道号“真一”,人称“肖真人”。此人在胭脂山上作法念咒七日,蝗虫遂扑向胭脂山上的一个山洞,如同吸入一样,浪潮滚滚,数日后方才收息。后来,在此洞口便建了座虸蛖娘娘庙。想必这虸蛖二字,便是蝗虫的神名了。虸蛖其实是蝗虫,就因这庙,镇子也才得名蚂蚱镇。说也奇,自从建起这庙,山里再没闹过大的虫灾。蝗虫不作害了,虸蛖庙里的香火却一直很盛,管蝗虫的虸蛖娘娘后来就演变成送子观音般的神仙了。到庙里来烧香的,多半为求子,还可占卜婚嫁。虸蛖娘娘实际上身兼二任,既是月下老,又是送子观音了。虸蛖娘娘的身上披挂了红色的斗篷,还有好多条红绸带儿,是还愿的香客们孝敬虸蛖娘娘的。据说在这里祈祷许愿灵验得很。
狗蹄子赶到蚂蚱镇时,正是日起三竿,漫天一片火红云霞。风吹得不紧不慢,很是可人。沿着弯曲的镇街,摊子挨挨挤挤地摆满了,乡政府门前的空场子里,里外三层,成了绕不出的迷宫。赶集的,背背斗的,挑筐子的,拉架子车的,碰碰撞撞,就连南方的缝鞋匠、修表匠也都被强大的商品经济的规律从小县城驱赶到这里来了。
狗蹄子第一个念头不是去买硫酸二氢钾,而是替桃花到蛖娘娘庙里去进香。
他穿过拥挤的集市,一路往虸蛖娘娘庙所在的黄土高岗上走去。进香的人太多,走不多远,就挤出了汗,进香的多半是些姑娘媳妇老婆婆,一半是花花绿绿,一半是黑糊糊的玄色。男人则相对要少。
山下摆开一溜儿香摊,狗蹄子比着问询了好几家的价钱,才在靠近庙门的一家香摊上买了一棒黄香,一沓子黄裱纸还有一对红烛。买好之后,便踩着凹凸不平的山路一路直奔庙里去。一溜风似的,将一群蹒跚的老婆子和年轻妇女们闪在了身后。听当当的磬声颤着铜音儿从庙里荡出来,从庙里飘溢出来的香烟味道也很是好闻。平常,他绝不会有这种感觉,或者根本就顾不上有这种感觉。
庙是很小的庙,四周没有庙墙,左右没有配房,就孤零零一座庙。老远望去,庙门像一只大张开的嘴。庙前长了七八棵苍翠的柏树。黄土山上能长活柏树,本就是一宗神灵的奇迹。烟雾般的香烟从庙里大漫出来,着了火似的,衬托得那七八棵苍翠的老柏树宛如立在云雾里一般,大有祥云瑞气的神灵气象。
进香自然不好背了大背斗去磕头。狗蹄子在庙前盘桓来回,在一根柱子下瞅中一处空闲地方,放下背斗,见一个嘎嘣嘎嘣吃着炒豆子的女人在那里坐着,狗蹄子就托靠那女人费心替他照看着点儿背斗。吃炒豆子的女人看看狗蹄子,没点头,也没摇头。狗蹄子就急急挤进了庙里。
烟雾缭绕中,只见一溜儿高高撅起的屁股和一簇簇点燃了的黄舌舌的香火。有个看不出年纪的道姑盘了腿,坐在神像一旁,时不时用一根戒尺般的东西敲击一只磬。那磬便发出徐徐的荡荡悠悠的悦耳之声。庙里的香火熏得狗蹄子两只眼睛辣辣的,只想流泪,透过烟气,约略望见一尊黑不呼呼的神像落座在神龛的五彩莲台上。神像身上披挂了红色的斗篷,还有许多红色的绸带,自然是还愿的香客们给披挂上去的,可见这虸蛖娘娘确实法力无边、神通广大。狗蹄子在虸蛖娘娘神像前跪下去时,捏在手里的黄香都被汗浸透了。
“你看这慌张的……”他咕咕自语。
旁边跪着的一个老婆子怪异地望了他一眼。
狗蹄子心想,桃花究竟要许个啥愿呢?他忽然想:桃花也该有个跟小水水子一样心疼的娃了。于是,他虔诚地焚香、燃烛、化裱……
望着眼前袅袅的轻烟,在心里一遍遍为桃花虔诚至极地祈祷。望着跳闪着火苗儿的红烛,他又想,在虸蛖娘娘面前,也该为自己许个愿才好:
“虸蛖娘娘啊。何发有今日就在你面前许个愿,你要真是神通广大,就保佑我何发有将来有一日能娶个像桃花那样的好女人,我来世里变牛变马也要报答你哩。”
从庙里出来,狗蹄子顿觉神清气爽,肋下生风,脚步从未有过的轻快。许了愿,犹如三伏天吃了剂解暑的凉药,眼睛都清水似的了。他走到那根柱子底下时,却一惊:他的背斗竟不翼而飞了,再看刚才蹲在那里吃炒豆子的那女人,因为早不见了踪影……
“背斗哩?我的背斗哩,谁个把我的背斗背着走了?!”他毫无目标地朝四下里喊。
没有人回应他……
他又绕着庙转了一圈,还是没找见他那只背斗的影子。要搁旁的时候,他说不定会泼口大骂,会窜遍整个镇子去寻找他那只能背斤的特大号背斗,会随便抓住背在人家肩头的大背斗,仔细看看是不他那一只。可这天,他并没这样做。一路下到山下时,心里的火气已平息了大半。尽管一路惋惜得啧啧连声,却反复地为自己宽心:“罢罢罢,该丢的东西咋也丢哩,破财免灾、破财免灾、破财免灾……”
他一路上这么咕咕哝哝地磨叨着,重又回到集市上时,蚂蚱镇的大集更加万头攒动,一片火红的热闹了。他这才准备去供销社买硫酸二氢钾。
我那天正好去到镇里采访。
自从我当上了陇中报社的记者的这两年间,极少回家,回来过几趟,也是板凳还没及捂热就又走了。其中一次还是陪同了从北京来的记者来的,上午来下午走,来去匆匆。这天我坐的是一辆报社的吉普车,路过镇南石桥,往乡政府去的路上,忽听有人朝车上喊:“存禄!存禄!”
是我的狗蹄子哥。
一看他的表情,我就猜得出他心里一定在说:“癞呱子啊,你狗日的,今天可把你这个比县太爷还忙三分的公家人撞上了。这大集没白浪一趟呢。”
我跳下车,看他满头是汗:“哥,你咋来了?”
“没想到把你可撞见了。今天总该回趟家哩吧?”他说。
“忙得很,可顾不上回,罢了再说。”
“我就知道。”狗蹄子一脸的失望,“都到家门口了么……”
我说:“今天真来不及。还要到乡政府去,和许乡长约好的,人家等着哩。”
“咋?屋里有狼哩?吃你哩?”狗蹄子朝吉普车上瞅了瞅,报社的司机老张揿开车上的音乐,邓丽君正在唱《何日君再来》……
“采访完还要赶回去发稿子,印报纸的事麻烦着哩。你回去替我跟桃花说一声。”
“要说你自己家说去。”狗蹄子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
又闲说了几句,我就急急坐车到乡政府去了。没想到狗蹄子竟一路跟到了乡政府。我和许乡长在许乡长办公室里谈话的时候,狗蹄子就一直在乡政府的大门道里蹲着。他还透过窗户里朝办公室里张望了两回,见我同许乡长说事。许乡长平时常去桃花尖检查工作不是今天这架势,脸上总挂着利害的威风,这忽儿,脸上是一片和蔼的笑容了,给我递烟递茶都是双手儿,我问到啥问题,许乡长就笑眯眯地回答啥问题……狗蹄子看了两次之后,见许乡长的目光往窗户上扫了一眼。就再不敢张望,老实地去门墩子下蹲着去了。他旁边立着一只特大号的背斗,却不是他遗失了的那一只。背斗旁蹲着个粗大汉子,正就着根大葱,喀哧喀哧吃一张干得发硬的锅盔。那背斗里装满了一种灰青色的石头,不是常见的石头,狗蹄子顺手从那背斗里拿出一块石头在手里掂了掂,比普通的石头沉。吃锅盔饼子的汉子瞪了他一眼。狗蹄子就把石头丢进了那背斗:“这位老哥,这啥石头啊,掂起来重重的,敢不是矿石么?”
汉子说:“铅锌矿石。”
“这能做啥用?能卖钱哩?”
“说的,这一背斗少说卖20块钱哩!”
“喔唷!老哥!你敢不是哄我哩吧?”
汉子喀哧地咬了一口把在手里的大葱,不再搭理他。
狗蹄子却不罢休,笑嘻嘻套问了一阵,才打问出“种石头就出自离桃花尖60里地的野狐沟。那里新近发现了这矿石。有能耐的人早闻风而动,在野狐沟都连着开了好几口矿井了。
狗蹄子直埋怨自己耳目闭塞。这么大个事居然一点风声没听说,万万不该的。人啊,穷不怕,就怕穷得连耳目都闭塞了,那才真没一圪渣指望了。他想细详地向那汉子问询清所有细节。那汉子却已吃完锅盔,两手拍打拍打,准备要走了。狗蹄子很有眼色地帮那汉子把沉重的背斗上了肩。
那汉子回头说:“野狐沟那面缺的是人手哩,你要若吃得了那苦,就去试活试活吧。一天苦下来,少说也挣个二三十大钱。”
狗蹄子自是千恩万谢,心想:这也是一条活人的路哩。
我从许乡长办公室里一出来,狗蹄子就迎上来,一把将我拉到一旁:“存禄,你要是还认我这哥,就听我一句话。你跟桃花结婚几年了?你在兰州上大学的时节咱就不说了,可你回到县里这二年来,你正经地回过几趟家?啊?桃花她还是不是你的女人?你说。”
“哥……”
狗蹄子却不容我说话:“人家不容易啊。存禄,你当谁是瞎子?人总要将心比个心哩,万不能坏了良心啊。人家一个女人家,在屋里撑门立户,图个啥?就图你一来不回家,二来不回家?三来还是个不回家?她就图背个空名声在屋里守活寡哩?你心里咋就坦然?啊!”
我看看腕上刚买的手表说:“哥,我真是得走了。”
“你走吧走吧。”狗蹄子气得一挥手。
我从车里探出头说:“哥,你甭生我的气啊。”
狗蹄子将脑袋拧转向一旁,只哼了一声……
狗蹄子在回到桃花尖去的那一路上,应是阴沉着一张脸的。回到家,我母亲小心翼翼地问他:“发有,你咋一脸的不受活啊?莫不是出了啥事了?”
狗蹄子气出三股地嘟囔:“半道儿碰上个贼!”
36、苦夏
伏前连下了几场透雨,家家的麦子长得都出奇好。桃花尖的男人和女人们的脸上见出了光泽和活泛。
从南方吹来的热风一阵没停歇过,呼啦啦吹过黄土地,吹得男人和女人们都少了瞌睡。连牛马发情的时间也比往年长,且疯狂。赶麦黄时节,在外打工的男汉们也陆续回来了,跟商量好了似的都赶在一个点儿上。有在兰州铺马路,挖地沟的。有在建筑队上打工的。有在餐馆里当伙头的,帮工的,还有在戈壁滩上挖硭硝的。当然其中也有叫人给骗了的,但居多的还是多少挖抓了些“光阴”回来了。事实证明,凡走外的,比守在家里的总路子宽展。况且各家种各家的责任田,除了播种“收获,平素也用不了多的人手。
那些穿了一色的囫囵衣裳和削价皮鞋回来的男汉们,纷纷登门来动员狗蹄子:
“发有,你死囚囚蹲在屋里有球的意思?世界这么大的,桃花尖算球个啥哩?麻雀肚子里的一颗米。你看我们,出外把光阴挖抓了,把该看的看了,把该玩的也玩了。你听说没有,城里女人跟咱乡里的女人就不一样,城里的女人可骚了。你知道啥叫个‘打洞’么?”
“打啥洞?”
“还有‘打飞机’。知道啥意思么?”
狗蹄子只是一个劲儿摇头。
“不知道吧,在城里,洗头洗脚啥的,都是生意哩。”
狗蹄子说:“洗头还要跑大街上去?家里就不能洗?”
旁人就笑话他是个十足的呆瓜。
“还有按摩女,那身上,就跟啥都没穿一样,听说是只挂一根布筋筋儿……”
对于如此这般的描述,狗蹄子如何都想象不来。只感叹眼前这世界变化真是大。他好歹也是条硬梆梆的汉子,又不缺胳膊少腿,走外的条件自然是有的。村里的年轻人也一再鼓动他去闯荡,可他至今没出山。实际是离不开这个家啊。家里有勾他魂儿的人哩,那就是他的兄弟媳妇罗桃花。她就像股紧吸着他的磁力。他和她天天照面,时时感觉着对方真实的存在。许多说不出的细微感觉就含在每一次闪烁顾盼中,包含在看似庸常平淡的家常话语中,他同她之间,似有什么在一天天、一点点地悄悄儿滋长着,像从盐根上生出盐一样……
里外忙碌一天,天一黑定,桃花把厨房的事收拾停当,引了小水水子到西厢房里早早歇息去了。平素,她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话不说,该说的也极有分寸,句句说在情理上。闲时也没走东家串西家的习惯,更不缠绕女人间的事非,实在闲得慌,就搜罗些活计来打发熬人的时光。
而摆在老两口子眼前的紧要事是:狗蹄子这条七尺大汉已打了6年光棍了,秋后无论如何得替他说下门亲,不能再拖延了。我父亲念兹在兹,四出打听寻访,但人急事不急,寻来寻去,紧忙碰不上个合适茬口。
狗蹄子的事尚无一点眉目时,何神仙的儿子屎蛋子却要结婚了。媳妇还是许乡长的千金丫头翠儿。
屎蛋子请下了全村人吃喜酒。给他媳妇送的竟是一只金壳子小手表,还有只屎壳郎大的金戒指。在桃花尖人眼里,这般礼品在以前如何也想不来的。屎蛋子脑子就是活络,前一阵,这家伙又在野狐沟开办起了铅锌矿。这一来就更财大气粗了。
屎蛋子的喜事办得自是红火热闹,闹洞房闹得那新娘子成了一滩红泥,三官庙前连放了三天录像,屏幕上活动的全是些碧眼黄瞳的高鼻子男人和女人,场面豪华,情节热烈火爆。打得头破血流,爱得你死我活。
狗蹄子看着刺激,时不时朝女人伙里偷眼瞅去,几乎每次都能和桃花的目光在半空中撞在一起,仿佛两人私下约定了似的。当电视上出现身穿三点式的女郎和一个赤裸的洋男人在太阳底下的海滩上抱着滚成一团儿的时候,看录像的汉子们便开始鼓蛹着朝女人堆里渗透了。这里哪里发出一声声女人夸张的小声惊叫和骚情的捶打唾骂。不用问,此刻定然是某个汉子的巴掌摸到某个女人的屁股蛋儿上……
狗蹄子再一瞥,桃花的影子已从人群中遽然消失了……
桃花先自回到家里,小水水子已睡得像只香瓜,嘴边挂着涎水。
我母亲问:“桃花,录像可放完了?”
“还没哩。”
“那你咋不看了?这早地跑回来做啥?”
“头有些晕,困了。”
说话间,狗蹄子的脚步声也响进了门道。
正要去给那头老母驴和小黑骡子添草的何佛留问狗蹄子:“发有,看完了?”
“嗨,把那有啥看头哩?真还不如多睡忽儿觉……”狗蹄子含混地喃喃,说着,朝西厢房窗户上似不经意地瞥了一眼……
西厢房亮着柔和的灯光。
他心里忽然踏实了,仰头看了看升在中天的将圆不圆的月亮,上了趟茅圈,又立在桃树底下响亮地咳嗽了几声,也像是故意咳嗽给她听的。
西厢房里的灯光却倏然熄灭了……
狗蹄子心头掠过一丝怅然,猫腰钻进了黑洞洞的仓房。
桃花尖的夜长得没边儿。
过了好大会儿,庄道上才嗬楞楞响过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说笑声和嬉闹声浮在脚步声的上面。定是录像放完了,散场子了,众人正各回各家。不知谁唱起了一支俚曲儿:
七月里个七,八月里个八,
骑上个尕毛驴儿回娘家,
我的大姐啊。
骑上个尕毛驴,走过包谷地,
包谷地里钻出一个当兵的,
我的大姐啊。
那个当兵的,吃的是野粮食,
裤裆里就掏出一个坏东西,
我的大姐啊……
给牲口添罢草的我父亲一听这不三不四的声调儿,就知是高丽铜那货,一股火气窜上脑门心,扔了手里的笸箩,大开了街门,窜到门口去骂:“嚎丧到野地里嗥去!”
高丽铜的声音从暗黑里尖出来:“噫?马槽里拱出驴嘴,管天管还能管住老子“屁?”
“你放屁了到茅圈里放去,少在我门头上放。”我父亲进了院子。
孰料高丽铜唱得声腔儿更高了:
头一下下疼,第二下下麻,
第三下下就像那个蜜蜂子扎,
哎呀我的大姐呀……
我父亲呸地往地上大啐了一口。
第二天,桃花尖的太阳照常升起,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然而,桃花同狗蹄子在那一整天里却都不敢彼此望一眼……
37、桃花进城
桃花来进城找我是坐了二虎他们的施工队里的一辆东风车来的。
二虎领着人在城里打了一阵家具之后,又不安份了,他看建筑业彷佛在一夜之间蓬勃兴起,便脑子一动,从桃花尖拉了一支建筑队连夜走兰州当上了包工头。大冬天的,十来条汉子挤睡在个填平的猪圈里,冻得乌龟似的缩成一团,工具就是十来把铁锨,先承包的活是挖地沟,那活儿又苦又脏又累。二虎想,靠这么小打小闹不行,得上大工程。他往海棠子家跑窜了几次,大概是何龙给他了一番仙人指路。二虎很懂得不花小钱赚不了大钱的道理,出手比一般人大方,所以很顺利地打通了关节,居然把三层楼的一桩工程包到了手。只是后来盖起的那楼很不成个样子,扯皮扯了好几个月,赶过年才勉强把工程款讨要到手,这在桃花尖众人的眼里已算了不起的成功了。
那天,二虎坐着施工的车,不但把桃花拉到了城里,还跑到地委报社楼下,手卷喇叭筒大声嚷惶:“癞呱子!我把你媳妇子送着来了哇。”
引得十几扇窗户里探出了许多脑袋。
吓得桃花苏溜地躲在了二虎身后。
我从编辑部窗户里望见躲在二虎身后的桃花。穿的是结婚时穿的那件紫红色条绒衣裳,胳膊弯里挎着一只包袱。身干子显得瘦小,梳理过的头发紧巴巴贴在头顶上。当时我真恨不得掩面从楼上纵身跳下去。
往宿舍里去的路上,我在前头走,桃花相跟着。
进了宿舍,她两眼神陌生。
我说:“也不嫌累得慌?把包袱放下吧。”
她就把包袱放在床上。包袱里是准备换洗的衣裳,还有一布袋炒豆子和山核桃,除此之外,桃花尖再没啥好捎带的东西了。
“早些时我来过一趟,可没见上你的人。”她喃喃,“这屋里亮瓦得很……”
“家里都好吧?”我端了脸盆准备到水房里去打水。
“好着哩,咱大咱妈都好,眉儿越长越漂亮了。发有哥也好着哩。小水水子说话也就上学了。地一分到各家,活倒消闲了,这阵儿,村里走外的人也不在少。”
我从水房里打了盆水来:“先洗一洗。我还得上班去,你洗罢先歇缓歇缓。”
她嗯了一声。
下了班,我拿了饭盆去食堂打饭。几个同事跟我开玩笑:“何记者,你狗日的金屋藏娇啊。”
“你悠着点儿啊。”
老盖那家伙也到食堂来蹭饭了,老盖一个人常住文联,负责编辑《黄土地》,那是一份不定期出版的内部文学刊物。老盖常打电话和我胡扯八咧地聊天。
他凑到我跟前鬼笑着:“嗨,伙计,董小姐那面要不要我去安顿安顿啊?可别撞车了。”
不料等我打饭回到宿舍时,听见了牡丹子的小声,她正在我宿舍里跟桃花说话儿呢。
“……怪不到的,早就听人说嫂子是贤惠了得的人儿,今天猛乍乍一见你的人,才知道众人说的是不虚,我真个是有福气呢。”是牡丹子的声音。
“啥啊,村里的人都说你在外头可见了大世面,成了人上人了。”桃花几分羞怯地说。
“说的,还不是一样的人啊?”
“那到底还是不一样,你看你,穿的戴的,明光照眼,跟画儿上一样。”
牡丹子笑说:“好我的嫂子哩,你才会说话得很。”
我推门进去,两手端了两只大碗,……子串了几个馒头。牡丹子有眼色地来接,倒是桃“有些惶然了,抬起屁股又坐下,看看我,又看看牡丹子……
“看样子,不用我介绍了吧?”我说。
“谁还用你介绍哩?梦里头都梦见过几百回的人了。虽说以前没见过嫂子的面,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牡丹子化过妆,眉毛描过,脖子里还挂了条项链。
桃花自然早听村里的人说起过董七少家有两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大的叫海棠子,小的叫牡丹子,海棠子嫁给了何龙,牡丹子离开桃花尖也早,都成个人物了。
牡丹子搂了桃花的肩膀,像亲姊妹般的亲热:“我早听人说嫂子贤慧哩,今天一见,才更知道了。”
我要去再打些饭,留牡丹子一起吃。
“算了,我将在宾馆里吃过,我就想到你这里来讨杯酽茶消消食,端端地就把嫂子碰上了呢。”牡丹子说着,从手袋里掏出一包绿莫尔,抽出一支,用打火机点着,“把你们搅臊的,尽顾着和我说话了,你们快趁热吃你们的。别管我。”
桃花看得两眼发直。女人还抽烟哩?这要在桃花尖,不就是女二流子么?
牡丹子只稍坐了一会,就起身告辞。
我说:“你急啥?坐你的。”
牡丹子说:“不是我急啥,我是怕你急哩。心里急,嘴上可又不好说。我得多少有些眼色啊,腾出时间来,好叫你和我嫂子亲热亲热啊。”
桃花的脸霎地红到了脖根:“你……再坐忽儿嘛。”
“真的不了,说好跟马局长说个事哩。”
牡丹子一走,我和桃花只是默默地吃饭。
桃花小心翼翼说:“刚才在我面前她还叫你的小名儿哩……”
“那有啥了?”
“我就听着怪怪儿的。没想到她就是董家的二女子,人是真格的漂亮,又天生一张巧嘴。喜欢人呢。”
桃花只在我宿舍里住了三天。
头天晚上。我说有篇稿子要写,吃过晚饭就到办公室坐着发呆去了,磨蹭到夜里十一点钟才回了宿舍。桃花已靠在床上迷糊小半觉了。
第二天我又是一整天的上班。桃花一个人在宿舍里闲得蹲不住,给我洗了衣裳,拆洗了床上的被褥。
到了第三天,手底下就再找不到可做的事了,更觉得城里的时光过得尤其缓慢,不像在桃花尖,鸡叫三遍醒来,一眨眼的工夫,日头就急惶惶落到西山背后了。
第三天傍晚,牡丹子又来转了一趟。她跟桃花拉拉杂杂地聊天。还非要拉着桃花出去走转。桃花本哪儿都不想去的,但拗不过,也就相跟着去了。
桃花大约有两年没进过城了。
她发现傍晚的陇中城比以前是热闹得多了,柏油马路两旁一律都新栽了高高的白色电线杆子,长长地挑出一盏盏蚂蚱眼形状的明亮路灯,沿街的商铺不但骤然间挤巴巴地一家紧挨着一家,而且各种的灯箱广告和霓虹灯广告闪闪烁烁,把这小城的夜色也装扮得有些光亮了。橱窗里的塑料模特儿摆出种种的姿势展示新款服装。电影院门前的海报上,色眼迷离的洋女人漠然俯瞰人来人往的大街。当然也有旧日的风景,如街头爆米花的,时不时蓬地一声炸响,吓人一跳。这里那里,飘出青年男女大声吼唱的声音,唱的都是流行的歌儿: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哦,日头从门前走过哦,还有《一无所有》……
行走在暮色里的街道上,桃花只顾傻呆呆地东看西看,她走在明光照眼的牡丹子身边,觉得自己实在像是个陪衬,人家有多白、多漂亮,自家就有多黑、多瘦。
牡丹子走一路还跟一路的熟人打招呼呢,笑得花儿似的,说的话也甚是流利自然且又妙趣。给桃花一种感觉,彷佛这陇中城里没几个人不认得牡丹子。
牡丹子拽了桃花去了一家卡拉OK,点了两罐可乐,要了一碟儿瓜子。桃花还是头一回到这种场合里来,十分不自在,心口子好一阵噗噔乱跳。牡丹子却像在自己家里一般,拿了麦克风,先唱了一首《何日君再来》。
桃花在一旁听得都有几分迷了呢。
牡丹子把麦克风塞到桃花手里:“嫂子也唱一个吧。”
“喔唷!”桃花急忙烫了似的往后缩着身子,连连摆手,“我哪里还知道个唱歌的哩?嘴笨得跟棉裤腰一样,生来就不会的。”
后来,包厢里又来了两个男人,是牡丹子的熟人,牡丹子同他们稔熟地开着玩笑,说的像生意上的事,又不像生意上的事,寒暄一阵之后,其中一个男人同牡丹子唱起了《夫妻双双把家还》,那男的嗓子十分难听,唱出杀鸡似的声音,桃花在一旁听着十分的聒噪。强忍着又熬煎似的坐了一会,就稀稀地坐不住了,悄悄对牡丹子小声儿说了几遍要回的话,牡丹子才放她出来了,一出门庭,桃花便如获大赦似的长舒一口气。
桃花回到宿舍的时候,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满心的不快,我看也没看她。
我生气地说她:“谁叫你满世界胡跑的?你还以为这里是桃花尖么?”
桃花想替自己分辩一句,却又什么都没说出口,只是鼻子一酸,眼泪就忍不住在眼眶里转开了花儿,她背转身去,作了掩饰。
第四天,桃花托辞说:“这阵子家里活计忙,我再住着心也不安定,想早些回呀。”
我连句挽留的话都没说:“这阵子我忙得是啥顾不上,等过一阵了我再回。”
桃花呐呐:“知道你忙,你就忙你的吧。”
我把她送到了公共汽车站,送她上了班车,乘客还没有坐满,司机还在四面八方嚷嚷着拉客。我心里到底有一丝过意不去,跑去摊子上买了一兜桔子来,从车窗里递给她。
桃花淡淡地朝我笑了笑说:“你回吧。”
桃花一走,我倒真松了口气。
傍晚的天气闷热难耐,我随便拿了本书看,却一行都看不入眼,隔壁的六弦琴声却叮叮咚咚响起来,还是那支《苏珊娜》,和弦的弹奏仍然像我最初听到的那么蹩扭。
一会儿,琴声停了,屠小红的脚步声轻盈地响出来,我的门大开着。她仍用两根指头敲了敲开着的门,以示礼貌:“可以进来吗?”
我说:“你看你搞的繁琐不繁琐,进来就进来嘛。”
屠小红进门,将一包话梅皇往我桌上一丢:“呶,给你夫人的。”
“人已经回了。”我懒懒地说。
“怎么回事?刚来就走啦?”屠小红惊讶地望着我。
38、政变
桃花尖在二虎回乡的这一年年跟前发生了一场“政变”。二秃子下了台,众人一致推举二虎当村长。
二虎起先推三推四,可经不住众人一再推举,才将脸一抹说:
“行,只要大家看我是个人,就是阴曹地府我也钻!”
二虎走马上任头一天,敲钟鸣号,将各家各户招呼到一起说:
“眼下,村里的地都承包给各家各户了。人一有了心劲儿,地里疯着长粮食哩。早上都不用出工了,也不用拉上架子车送粪了。可话说到脚后跟上,粮食也不过就是个粮食,不值钱。种田之外咱还得思谋思谋旁的法子挖抓些光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能走外的,你就走外去,能日鬼捣棒槌的,你就到外面日鬼捣棒槌去,不想走外的富余劳力,咱就组织起来搞副业。”
说过这话的第二天,二虎不知从哪儿日鬼来四辆手扶拖拉机,做梦似的就实现了机械化。先送粪,后犁地,再耙地,活干完才走。桃花尖的人头一回像招呼地主一样招呼二虎:
“掌柜的,你就把那帽子歪戴上,嘴里把纸烟把把儿锲上,在跟前指挥着就成了。你总不能像陈永贵,头上老包个羊肚子毛巾,你就把呢子衣裳穿上,姑娘领上,好好抖一抖。”
接着,二虎让村里有力气的烧砖头、烧石灰。精明些的,进城搞油漆的买卖。他自己领人租了两辆汽车去贩黄牛,贩黄豆,还从宁夏换回大米来,到市场上转手倒卖。没几天就把个死气沉沉的桃花尖折腾得有点红红火火了。
那日,屎蛋子的泰山大人许乡长到村里来,二虎在家里酒饭招待,他拳打天下,酒量惊人,喝着酒,跟许乡长以及在座的几个乡镇干部说了一番很过分的醉话:
“……你们以后到咱桃花尖来,我六菜一汤招待,有酒喝,愿意吃的,吃;不愿意吃的,回……你们干部,过去是保甲长,现在叫书记、乡长,其实一球回事,都是给皇上要粮草的……以后有任务就交下来,我按时完成,你们想吃啥了找我,想喝两口,找我,其他事就甭来找我……”
二虎酒醒之后,大龙说二虎:“你听你说的那些话吧。人狂没好事,狗狂拉稀屎。出头的椽子先烂哩,哪朝哪代不是要杀富济贫?再来个运动,你不是刘文采,就是黄世仁啊。”
二虎说:“怕个球哩,再打入十八层地狱,咱不还是个农民?”
到了年底,光是搞副业一项就挣了5万多。二虎亲自到银行提款,跟银行的人说:“麻烦给咱换成一块钱一张的票子。”
5万块钱在地上摞起高高一大堆。用了两只提包提回桃花尖。
二虎在村里的大喇叭上吼叫了一阵,叫全村每户来个主事人来分钱。
一圪堆崭新的票子高高地码成好几大摞,看一眼也吓人。
二虎这家伙到底是闯过社会的,做事到有魄力,而且用脑子。他那次那进城来找我,正好省报下来个总编室的老记者,二虎就在陇中城天津包子馆做东,请我和那省报记者吃饭。饭间,二虎当了那高度近视的老记者的面好一通的胡吹冒撩,把那老先生的眼睛都说直了。第二天,二虎还陪那记者到桃花尖去了一趟。
没过几天,省报的头版头条就登出一篇新闻来,大大的黑字标题是:《桃花尖实行责任制一年致富》。
我心里直骂二虎这小子混帐。
消息一登报,蚂蚱镇的许乡长就坐着刚买的一辆红色桑塔纳一路杀到桃花尖来,把二虎从被窝里捞起来说:省上要来大人物了。二虎问是啥大人物。许乡长说:省委书记。
二虎喔唷一声说:“怪不得昨天我梦见一只老虎。”
省委书记并不是头次到桃花尖来,以前就来过两次,头次来,去了高丽铜家看了看,高丽铜就成了省委书记亲自联系的扶贫户。省委书记二次到桃花尖来之前,乡里和县上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无偿给高丽铜突击盖了三间瓦房。省委书记还叫人给高丽铜捎了一笼长毛兔种来,叫他走养兔致富的路。书记派来的人放下兔子一走,人还没有出村,高丽铜就将长毛兔种炖到了锅里,就着二两老酒,吃得个满嘴流油。给兔子拔草的婷儿回来时,已剩了一堆兔骨头,婷儿一屁股坐在地上就哭了。事过半年,听说省委书记又要到桃花尖来,县上、乡里着了慌,忙叫人临时弄了一笼长毛兔来,连夜送到高丽铜家。这一笼兔子二天又变成了高丽铜的下酒菜。省委书记第二次来过桃花尖之后,高丽铜身上多了一件半新不旧的粗呢子大衣……
这次,省委书一来,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自然不能不来。
二虎那天可是风光了,跟省委书记坐在一只土沙发上拉家常,省委书记问他是如何带领桃花尖的众人致富的。二虎一张利嘴滔滔不绝道来,有的是有,没的也是有,拾到篮子里都是菜。还举出例子来印证。他这一手是从省报老记者那里学来的,那老先生采访二虎的时候,总是说:“等一等,你能不举个例子?”二虎起先不明白啥叫例子,后来知道就是举出实际的人物和事来增加说服力,一个生动的例子往往比多少话都顶用。于是,二虎就给省委书记举例说:“咱桃花尖,原老少总共21条光棍,有道是:破皮袄拉得土扬哩,光球敲得炕响哩。现在可好了,媳妇子全娶进门了,过去,一到夜里野汉子就爬墙越院,害得家家户户把狗养上也挡不住,现在就完全是不用了。”
省委书记听了忍不住大笑了一阵。
二虎装作害怕的样子问:“喔唷,我把话说错了吧?”
省委书记说:“你讲得很好。很好,不过,咱西北人的一大毛病就是不会经营。比如说,咱这地方出好大豆,却没人造腐竹。吃的腐竹全是外地进来的,干看着大把票子叫外头的人赚了去。你说可惜不可惜呢?”
二虎眼珠子骨碌一转,立马顺竿儿爬:“喔唷,我正思谋着要办个工厂哩,叫每户人家选一个人到厂里做工,一律给发工资。”
省委书记连声说:“好好好。那我顺便给你提供一条消息,你们县里正好来了一笔扶贫贷款,可就是谁都犹犹豫豫,不敢贷,二虎你敢不敢?”
二虎一拍胸脯:“咋不敢?咱贷。贷了款,咱就照你说的,办他个腐竹厂。”
闲说了一会,省委书记一行人坐上几辆小卧车,碾着一溜黄烟离开了桃花尖。
文章来源:李本深作家书法家工作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