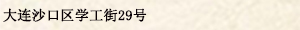林甸水利工地逸事乡愁林甸记忆征
“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水利工地逸事作者张鹰文革前和文革初,我正在生产队里当社员。那时候,我还没成家立业,因为是单身小伙,队里出工修水利,就少不了我。那些年,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年轻人辗转在林甸这片土地上,挖沟、修渠、筑坝,出了不少力,每到一处,不但活干得漂亮,而且,总会演绎出一些浪漫而又有趣的事来。
毁弃的文物
年的冬季,林甸县统一在各公社各大队抽调一部分劳动力,修筑东升水库大坝。我们大队十几名民工坐着马车向胜利出发。那是因为乡间土路坎坷不平,马车行驶缓慢。当晚在县城的南大车店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才到胜利。我们六个人被分到一户姓X的人家住宿,这家是三间草房,中间是厨房,东西屋都是南北炕,六十多岁的老奶奶领着儿子媳妇和十四五的半大孩子,他们一家四口住东屋。我们六个人住西屋的南炕,北炕堆放着她家的一些杂乱东西。一切都安排好后,指挥部领导把我们集中起来开会,要求我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积极完成每天的劳动任务,要搞好群众关系,不要无故打扰老百姓,工余时间不要到处乱走,避免和当地妇女来往,以免引起不良后果……总之,我们是半军事化,对每一个民工要求极其严格。
那时农村还没有电,家家都在点煤油灯。我们每天收工吃完晚饭回到住宿的地方,就已是点灯的时候。而我们的屋里没灯,夜里十分不方便,特别我每次出来都带几本书,总想在晚上看一会儿。于是,我就偷偷地找我熟悉的施工员要几只蜡烛解决照明问题。
一天收工回来,发现我们住的屋点着蜡烛,进来一看,一个人把蜡烛沾在窗台上倚着我的行李在看书。见我们进屋,他轻盈地跳下地笑着说:大哥,你真了不起,干这么累的活,还带这么些书看。我看着他怔住了,他是老奶奶的孙子还是孙女?那红扑扑的脸蛋,俏俏的眉眼,一个活脱脱的小丫头。我指着他说:你……?
他愧疚的样子说:我没弄脏你的被,也没翻你的东西。
不,我摇摇头说:不是这……,你……你是女孩子吧
他一愣看着我问:谁说的?他瞪大了眼睛很惊讶的样子看着我。
我说:看你的长相啊。
他嘟着嘴很不高兴地说:你也这么说。
你不是女的?
是不。你看。说着他踢踢腿,抡抡胳膊。
打那,我们和小胖子成了朋友。那正是寒假时节,我白天出工后,他就在我们屋子里看我带的书,我带有几本文学杂志《收获》以及长篇小说《红旗谱》《战火中的青春》还有一本《漫谈林海雪原》。
我们劳动的地点是那条横亘在黄家泡子南侧的土坝,当时,刚露出冰面不足一尺高,工程技术员说如果不加高,一旦遇到洪涝灾害,大水就漫堤而过。这年冬天是趁冻,在堤南的一个小土岗上放炮炸开冻土,我们把冻土运到堤面上,待到来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冻土开化,再派拖拉机来碾压,然后铺沙石固坝体。这次专门有一个爆破组,放炮炸冻土。他们放一次炮,炸开的冻土块足够我们一百多民工搬运两三天。那时没有机械运输,炸开的冻土完全靠人工搬运,如果冻土块太大,还得人工用镐刨成小块。我们搬运冻土块就是采取用土篮挑,用网兜抬,也有的用人扛。
有一天早上,一走进放炮的现场人们全愣住了,那杂乱的冻土块中,有许许多多死人的骨骼,那吓人的骷髅,仰着空洞的眼壳,呲着那整齐的牙,像在对面前的人们诉说着往古的悲哀。还有马的颅骨和肢体均已全是森森白骨,锈蚀的战刀和铜器,残破的瓷碗和陶罐,桦树皮的刀鞘等,这些乱糟糟的尸骨和兵器在冬日的阳光里显得陈腐而阴森的寒光,这里是古战场,还是军人栖息的兵营,他们遭到了怎样的际遇?有的人被这一切吓得躲得远远的不敢近前,我们几个傻小子觉得好玩,就毫无顾忌地走过去,看那些腐朽而又陌生而又惨白的骷髅像在对这个世界倾诉着什么。那时,我们这群人里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些的东西有多么珍贵,而我们这些幼稚而又单纯无知的年轻人只是觉得稀奇古怪只想看个究竟。当时,工地领班的让我们胆大的把那些骷髅和白骨捡到一起,然后装到草包里让人运到沼泽深处,其他的那些锈蚀的器皿,谁愿拿谁就拿走。有的人觉得是死人的东西,让人丧气,就在当地砸碎和泥土一起堆向大坝。也有觉得好玩就捡了陶罐或锈蚀的战刀,还有铜铃和铜钱。我们几个捡了几个陶罐和青花瓷碗,还有一把绿锈斑斑的小铜壶。
回到住处,正在屋里看书的小胖见了表现出很喜欢的神态,我就给了他一个陶罐,其余的我们就擦净了放在了窗台上。
那是一个上午,一个工友搬冻土块时不慎滑倒砸伤了我的脚,工地卫生员给我上了药包扎后,我回驻地休息。一进院子,就听到家里的老奶奶在大声吵嚷着什么。我放慢脚步听到小胖争辩说:这么好看的东西你为啥都给摔了呀!
老奶奶大声呵斥着孙孙:你这个小孩牙子,哪里懂得这些,这些物件都是死人的葬品,放在咱们屋里多丧气呀。
我听到他们的对话,知道了是为什么在争执,就赶紧进屋。小胖见到我,就表现出是愧疚的样子,嗫嚅地说:张哥,那几个罐子和壶都被奶奶……
胡奶奶见了我也还是气呶呶地样子,毫不客气地对我说:孩子,那些让人丧气的东西让我摔了,哪壶也砸了。我愣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也说不出什么,是认为她砸的对还是不对?我毫无主张。但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责怪老人家。我只是苦苦地一笑说:没什么。这东西不好就……
你看你看,你张哥是听话的人。胡奶奶笑了,那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了。她笑得很得意,肯定了自己销毁这些东西的正确性。对于这件事。由于那时我对文物的无知,当时一点也没感到痛心,只是一年后见到一位文物普查员,他从揹囊里拿出新石器时代的石箭头,还有大金时期的铜镜,当我对他说起胜利大坝的那个场面时,他惋惜的直拍大腿,那表情比失去万两黄金还痛心疾首的样子。这时我才意识到当时自己的无知和大意所酿成的后果是多么让人懊悔。是啊,历史上就有好多文明毁于粗俗和无知。许多事情发生在你面前的时候因无知和粗俗而失于保护或亲手催毁,可是过后一旦经智者提示,后悔也无济于事了。那再也难以遇到的古战场,再也难以遇到的古文物。失于无知,毁于无知。我难忘的胜利大坝呀!
民工的爱情
那些年,在林甸挖排水干线的工程是一直没停过,有一年我们花园公社的水利民工转战到东风公社的一个大队的一个小队挖排水壕。我们大队的十多个人住在一个单身汉家里。这比住在有男有女的人家要方便多了。说话睡觉都比较随便。我们这些人里大多是二十上下岁的小青年,五十岁的只有那么四五个。这些人里什么嗜好的都有。我自然是带几本书在闲暇时间看,二队的老刘头带着二胡,虽然不会识谱,却能拉得有板有眼,五队的小张好下棋,闲暇时,就会和戴小子两人将个没完没了。王二是个赌徒,一副扑克找几个人玩到半夜。
每天收工吃过晚饭,老刘头会坐在炕里的被子卷上,拉一阵二胡,什么《月牙五更》《孟姜女哭长城》《苏武牧羊》。人们就这样打发工余的寂寥。一天,一队的小张,凑到老刘头跟前问:刘叔,你还会拉什么曲调?
老刘叔一愣说:我这是靠那些年演皮影戏硬学了一些杂乱的曲调。皮影、评剧、二人转也都凑合。
记得当时小张唱了《夜宿花亭》中的高文举在花亭的那一段。声韵高亢有力,洪亮悦耳。二胡配得也相得益彰,韵律有加。有了小张的演唱,开展别样活动的全都停止了,一个个傻子似的两眼盯着小张,听他有板有眼地唱评剧,唱二人转。一天,他唱《杨八姐游春》,这一出戏表现的是天波府杨八姐游春的时候,被当朝的天子遇见了,见八姐俊美漂亮,就想把她娶进宫内做妃子。那时天子一句话谁敢违拗呢?没办法,八姐就采取要彩礼来难为当朝天子。小张所唱的就是杨八姐要彩礼那段:
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月,
三两清风四两云。
五两烟灰六两气,
七两火苗八两琴音,
人的影子要九两,
太阳的火光要一斤。
四棱鸡蛋要八个,
三搂粗的牛毛要十根。
要个镜子比天大,
要个洗脸盆子比海深。……
小张正唱得高潮起伏,突然,屋门一下子开了,门外齐刷刷站着十几个男男女女。既然门开了,这些人索性就大胆地走了进来,该上炕的就脱鞋上炕,该站着的就在地下站着。这阵势把小张弄得愣住了。人们进来后,有人喊了一声:别空场,接着唱。小张很大方,就接着唱下去。那一晚小张一个人唱到半夜十二点。从此我们的宿舍成了娱乐中心。每天吃完晚饭,除了我们的工友以外全是那个屯子里的男女在我们的宿舍挤得满满的。我发现每天来得最早的是一个姓赵的闺女。她长得瓜子脸,大眼睛,体魄丰满。几天以后,她来时会带来一暖瓶开水,给小张喝。时间长了,她中午也过来,很主动地给我们宿舍打扫卫生,或给小张洗衣服,我们也都跟着借光。
那次正赶上端午节,工地晚上提前收工搞会餐,赵姑娘就暗度陈仓偷着在半路上把小张接到他们家去了。打那,小张时常就去赵姑娘家。就在我们那次转战别的公社时,小张就被赵家留在那个屯子了。听说两人是秋季结的婚,并且,过得很甜美。农村青年对爱情就这么简单而热烈。只要自己爱上了对方,就很执着地去追求。
老倔子耿大叔
年春天,被派到富裕吉斯堡参与引嫩工程的建设。我们向前公社被称为红二连,扎营在吉斯堡的西面一个岗地上,这里是个乱葬岗,荒草间隐藏着许多坟墓。我们的宿营地就在乱坟之间。这里不光我们一个连还有其他连,那一幢幢简易宿舍有好几排,几百人的宿营地也是很热闹的。营地的大喇叭和工地的大喇叭遥相呼应。除了播放革命歌曲就是毛主席语录,再就是播发工地各连队和班排之间的进度或者是好人好事。我们的班是一色的地富子弟,只是班长是一个贫农的后代。我们这十二个人是尖刀班,每人每天八立方土,从河底挑到相距五十米的大坝上。那时相当地辛苦,一开始两百斤的土篮压得肩膀红肿,半个月后就好多了,而且能做到天天保证完成预定任务。因为我们几个干活实在,一天,连队特派我们三个去帮炊事班打烧柴。我们到离工地不远的一个水泡子边打芦苇,然后,拉到食堂前的空地上晾晒。我们是每天上午一车,下午一车。一天傍晚,装了满满一车芦苇往回走,在泡子边的砂土路上另一个连队的一辆拉柴车陷住了。我们过去帮着推车,他们领着打柴的是一个姓王的小班长,领着一位姓耿的大叔和三个小青年。耿大叔一脸大胡子,五十多岁,听说孤身一人,他当年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还负过伤,人和他的姓一样特别的耿直。
我们四个人过去加上他们四个差不多就能把陷住的车推出烂泥道。我们过去时,赶车老板把马叫齐,我们几个也一齐叫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第一次那车就像钉在了地上,纹丝没动,第二次,又叫齐了号。刚一呼叫。耿大叔突然喊了一声:停!我们都愣住了,转过脸看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他指着一旁站着的小王那边说:咱们都过去喊口号。
小王看着他不解地说:那怎么能行?
他说:都像你似的喊口号车准能出去。
小王说:不推咋能出去啊。
他说:那你为啥不推呢?
小王红着脸说:我给大家鼓劲。耿大叔说:大家都站在那鼓劲,你一个多孤单。
大叔把小王说得满脸通红,蔫蔫地也过来一起推车了。这一次叫齐号把车推出了烂泥道。
耿大叔老倔子的外号是出了名的。他们的宿舍离我们不算太远,那边要是大声说话我们这边都能听见。一天晚上,我们听到那边有人在大声吵嚷。我们好奇地跑过去看。发现有三四个人围着耿大叔,在指责他什么。我们到跟前。就听耿大叔吵儿巴火地说:我有什么错,我让大家都喊毛主席语录有错吗?
你为啥压制革命小将革命积极性。对方指责他。
老人家急了一跺脚说:别拿这种话压制我,我他妈革命的时候,你爹还没下生呢。
他不老实。一个大个子喊。把他压起来!他的话音刚落,只见耿大叔“嗖”地从门旁抄起一把铁杆烧火棍,呼呼地就抡起来。他这一通比划,一下子把几个人全吓跑了。耿大叔停下来喘着粗气说:这几个小杂种,想革我的命,是不是看走眼了。我凑过去小声问:大叔,你会武术啊?他呵呵地大笑起来说:你看我这是武术吗,就这么一通瞎比划,就把他们吓跑了,你说这些胆小鬼还能革命吗?
之后,我们和耿大叔搭伴在那片苇塘一连弄了五天烧柴。他真是个耿直宽厚的老人。他给我们讲在朝鲜战场战友牺牲时的那种悲壮。他潮湿着眼睛说:他们就在那颗炮弹落下来的那一瞬人就没了……他是个没儿没女孤独的老人,可他不靠国家照顾,他说和战友比,我还活着,我能干就自己干吧。一个了不起的老人,一个高尚的老人。从引嫩分手后,再没听到老人的消息。四十七年过去了,不知老人家还在否,无论在人间还是天堂,都祝福他老人家吉祥如意。
西邻之女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我们这伙挖土挑担的水利大军驻进了刘XX屯。房东是非常慈祥的两个老人,我们住在他们的西屋。老妈妈每天都给我们烧一大铁壶开水。我们时常给她往屋里抱柴,扫院子,上井台给她挑水。我们每天都在疲惫和愉悦中打发时光。一天,老天下起了大雨,这是我们民工最得意的日子,躲在宿舍里打扑克,吹大牛,痛快淋漓地享受这个雨休。近中午,雨渐渐地停了,我出来到那个用秫秸夹成的厕所里解手。看见院子西面的邻居家的两间房被一片汪洋给包围了,水都淌进屋里了却不见有人出来放水。我们平日里天天在工地施工,没注意这一家是怎么回事。我是个好事者,出了厕所跳过矮矮的院墙,过去推开了屋门问:有人吗?里面一个人有气无力地回答:有事吗?
你家房子被水淹啦。我边说边进了里屋,屋里一片灰暗,是因窗子胡着一层窗纸,只有一小块玻璃,透进一束光亮,使躺在炕上的人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她听见我走进来,艰难地欠了一下身子,我发现是个四十左右的女人,那面容十分憔悴。我说:大姐,你家的房子被水泡上了,屋里也进了水。
她说:没办法,没人放水啊。
我问:你咋啦?
我病了。她有气无力地回答。
我问她:医院啊?
她长出了一口气说:不用,过几天就好了。我叹口气走出来,那浑浊的水仍然还往屋里淌着。我回到宿舍喊了小赵,还有小付,他俩问:干啥?我指着西面的邻居说:那家被水淹了,帮他家放放水。站在厨房的老太太听了叹口气说:一个孤单的人啊,欺负她可有人,帮她就没人了。听老人家简单的诉说,我揣测这一家隐藏着很复杂的内容。先不管那些,先帮她放了水再说。
我们在她家的南面园子里挖了一道沟,穿过院前的一条村路把水放进了一个大坑。我们回来又到他家门口把流进屋里的水用铁锨都泼出来。她听见了动静下了炕,扶着门框说:谢谢你们啦。
我说:大姐,你好好休息吧,这点小事不用客气。
我们刚回宿舍没一会儿,就有人吵儿巴火地找上门了,来人粗声大嗓地问:你们谁把村里的道给挖了趟沟。我出来回应说:我们挖的。
他横瞪着眼珠子问:为啥?
我说:西院那个大姐家房子被水泡上了,我们就帮她放水在道上挖了一趟沟。
他白了我一眼,哼了一声说: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然后,又提高嗓音说:把沟给填好啊。
我说:这你放心,放了水,我们就去填上。他气哼哼地走了,房东大娘“呸”地吐了一口说:瞅他那样能吃人。
我问:大娘,他是谁?
队长呗,除了他谁能这么横。
第二天,指挥部的施工员过来对我说:小张啊,头头让我告诉你,咱们任务是挖好排水干线,别为旁人的事扯大了。我问他:我扯啥事了?
他说:你离那个女的远一点。
我急了说:我们就帮她家排排水,咋能扯出这么多呢?我要是帮你家干点活,你是不是在打你妹子主意啦?我这句莽撞的话说得他立时就脸红了。瞪大了眼睛瞅我。我赶紧道歉说:对不起,说句笑话。他“嗵”地打了我一拳说:你他妈早说啊,何必让我妹妹嫁给了个哑巴。一旁的人全被他的话逗笑了。
第二天,我们照常出工挖渠,一天中午,收工回来,炊事员告诉我:有人请你们吃饭。
谁?我惊讶地问。炊事员说:西院的邻居。
我说:你别拿我闲逗乐子。他一笑:真的。没一会儿,那个女的真的过来了,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让人眼前一亮,没了那天的憔悴,而是一脸的灿烂。她说:你们几个上我那吃吧。我说:大姐,谢谢你了,我们食堂也做好了,不给你添麻烦了。她愣愣地站在那,看了我好一会儿,苦苦一笑转身走了。没一会儿,端着一盆小鸡炖豆角,还有一瓶酒,放在食堂的锅台上,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走得浑身是气的样子。
一个多月的工期很快就结束了。那一段排水渠完成得很令指挥部满意。一个晴朗的早上,我们开始装车准备去别的工段。大家都在欢声笑语地收拾东西,同时又与老房东挥泪告别。我们的马车还没出院,西邻那个女的就行色匆匆地挎着柳条筐赶过来。筐里装着香瓜,我说:大姐,你这是干啥?
她说:给你们路上吃。我推辞说:大姐,你留着吃吧。
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说:你一个小孩牙子,怕药着啊?我被她的话一下子就噎住了。我没法再说什么了。她也没再说什么,把筐放在车上就转身飘然而去。我喊她:大姐,你的筐。她头也没回说:你们谁看着有用就留着吧。
更多好文,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林甸县丛家窑,成长在花园乡。曾任花园乡中学教师,哈尔滨正大集团办公室主任。目前退休在家,是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往期精彩内容直接点击阅读
复活精神的黑土地(“纪念林甸垦荒60周年”系列报道之一)
急!!!寻人启事!
老垦荒队员的林甸记忆(“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林甸,梦开始的地方
我的中学时代(“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林甸,那些光阴的故事(“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父亲的牵挂(“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家园(“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扬起文学的帆(“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林甸乡村工作记忆点滴(“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那些年,睡在通铺的兄弟(“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老街风景(“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马车时代(“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西门外也有个北大坑(“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我要谈谈理想(“乡愁·林甸记忆”征文)
刷爆朋友圈,“鸟叔”吴志林的拍摄现场太震撼
特别提示:“林甸往事”自从祭出人间凶器之尿道扩张器以后原创当忠诚遭遇绝对我想对你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