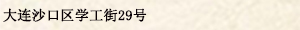散文两世的情谊
两世的情谊
作者:寒木
一、从陇西高原到滇南山野,再从滇南山野到陇西高原,我就像一片树叶,或者一叶扁舟,在现实的风波里或生存的海洋上飘荡,走了那么遥远,时间那样漫长。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走出陇西高原,从来没有迈出西海固的人来说,真是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我的心田旱渴缺水,我的胸襟窒息缺氧,我真正的感到了疲惫与劳累。
在漂泊了这么久之后,我终于规矩的跪在了祖坟边上,跪在了父母的丘墓前。
坟墓荒芜,杂草丛生,斜阳的余辉洒在秋草上,让人觉得沉寂寥落,静谧萧索。天高云淡,朔风飒飒,如铜丝般的声音在耳际萦绕,轻轻的山风从塬头上掠过。这是陇西黄土高原的边陲,这是人烟稀少的北方——我的故乡,我的流放之地与栖息之所。
有一个都市朋友曾看着我黑红的脸膛问道:你们那里是不是离太阳很近很近,是不是一年四季都在刮风?你们是不是严重的缺水,从来无法沐浴,也不洗脸?你们是不是两个人穿一条裤子,或没有可以铺盖的被褥?我想说,看惯了黑魆魆高楼的都市人,你懂什么叫天高气清吗?看惯了都市阴谋嘴脸与眼光的人,你能体味陇西高原的憨厚与和顺吗?唱着骚歌搂抱跳惯了摆尾舞的步履,能攀上黄土高坡的羊肠小道吗?充斥着靡靡之音的耳朵,能聆听得婉转悠扬的邦克声吗?我敢断言,不是先秦之民不能体味诗经;不是楚地之材,能以理喻离骚;生在都市的小市民,你永远也不能理解黄土高原的厚重与沧桑,哪里能听出山风的韵律,飞鸟的歌唱,还有花草树木的私语呢?
我的陇西啊,我的故乡,适合好人生存的黄土地呀!没有隐瞒,没有遮蔽;一切都是那么显而易见,那么明白无误。——毫不含糊的北方,大度的北方,让人一眼就能洞彻底细的北方!
有黄河从你的胸膛上流经啊!有长城从你的血脉上横贯!险隘比邻,关山雄踞。没有迈出都市环形路、逃离灰色天空的人是永远无法理解与感受她的辽阔与邈远。裹挟在车流里,鼻孔里塞满了二氧化碳的人,也是无缘顿悟与享受她的清逸与静谧!
我不是阿林(伊斯兰学者),跪在父母的坟墓前,惭愧的只想流泪。先上个坟吧,这是穆斯林男人游坟的惯例。选了几节自己诵读的不很熟悉的《古兰经》章节,深感声音微弱而纤细,沉寂而落寞;颤颤巍巍,随风飘落。不像那些伊麻目(教长,或有伊斯兰知识的人)诵读,那么婉转悠扬,那么高亢嘹亮。我在想,父母一生是农民,生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无常(去世)了又睡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心胸如土地一样平坦宽阔,脊梁如山脉一样高峻峭拔,平静的来了,宁静的走了,只留给我们许多的念想与教诲。
看着眼前逐渐夷平的墓丘,想想人最后的归宿,真的,人们究竟一天在忙碌什么,争夺什么,撕扯什么呢?
我也是从北跑到南,再从南跑到北的?
世上有几个人曾深刻的来到这里,曾仔细的想过这些隆起的土堆就是人最后的归宿呢?有的人可怜的就连这样一个所在都求不得,那么你在世间还逞什么强,蛮什么横呢?
回想我这短暂而冗长的生存之路,我真的很幸运,生存中竟没有遇到一点坎坷与挫折,艰难与困苦,路比我可敬的父亲平坦许多。我没有受过整,没有挨过斗,不但如此,竟然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尊敬,我应该知感了。我一生除了没有钱,什么都有,老人的爱,儿女的敬,亲戚的关护,邻居的和睦。虽然我可敬的父亲抛下我太早,可亲爱的母亲却陪我走了那么长的一段路程,使我在人生的路途上总是感到有温暖的依靠,从来也没有体会到孤单与寂寞,特别是当生存的风风雨雨向我袭来的时候,母亲凭着她精明的思维和丰富的阅历,让我在呵护中长大成人,变得成熟而懂事。因为我的养尊处优,纵然已到了知命之年,可母亲的离开无疑在我如折断了远航的桅杆,一时在生活的海上变得软弱与怯懦,萎缩与无助。
膝下有三个儿女,他们小的时候委实可爱,在你的身边就像小鸟飞来飞去,给你增加了人生无限的趣味,让你觉得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阳光,盛夏的火焰在燃烧,秋天的清凉在抚慰,你着迷的在这个顿亚(世间)上奔赴,你为了你可爱的小鸟,幸福总是充溢了心胸。
可是现在你突然觉得,任何儿女都是活埋老人的人。
不知谁说出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掩埋了父亲,儿子才能长大成人!我相信这是一句真理!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们都会死去,既然他们都会长大成人,儿子终久会长成老子,女儿总会成熟为妈妈,孙子总会变成爷爷。我们曾经历的他们一定会遇到,我们曾做的他们说不定还会重复,这样想来我们有什么好怨的,又有什么好恨的呢?“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只要他们成长起来,我们的任务也就交待了,他们会在我们这里学会做儿女,我们会在他们那里学会做老人,这是人类长河淘洗的法则,同时也是成长的教诲,我们只需虚心的聆听,规矩的遵循!
当我第一次如父亲抱起孙子一样的抱起鲁格曼(孙子的经名),就在想,人呀,应当感恩图报,每饭不忘。我们与伟大的造物者之间签订的那份合同也许就快到期了,说不定哪一天会在父母的坟脚下又突然的隆起一个崭新的土堆……
生命在世上存在的形式很多,但有思想的却很少。有的人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可他们从来也没有与伟大的造物主建立起一种关系,就是主仆的关系。——认识了自身的那个人,他认识了伟大的造物主——说的就是要人了解自己,要自始至终摆正自己与造物主的位置,要度好自己的长度,要絜好自己的高下。
人是渺小的,是卑俗的,是无知的,也是妄为的。尔扎贼俩(魔鬼)之所以永远没有忏悔的机会,他并没有别的罪恶,他太傲慢了,他只是忽略了谁是主,谁是仆的关系,他成了火狱中永久的烧柴……
就说我家族的这块坟地吧,我曾举意用一块肥沃之地兑换它,之后施舍给整个庄子,让后来亡故者有个安息之所。但是堂兄弟不换,他把地犁到了先人们颜面跟前,牛蹄子从先人的头顶上掠过去。他在努力的与死人争夺着地盘,他觉得种的越多会收获越多,不停地削小着坟地,可是他不懂一个道理:伟大造物主给谁吃谁就有所收成;不给谁吃,谁就是把先人们全挖出来晒下种粮食,仍然缺吃少穿。“况且人吃土地一辈子,土地吃人一口而已。”
可是有的人,出生在没有信仰的家庭,却懂得了许多道理,为整个人类做出许多有意义的事业,让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是他们与真正的信仰失之交臂!
譬如毛泽东先生,他不亏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的革命就是把信仰注入到每个中国人民的心中。他告诉全国人民,将来定有一个大同的世界,让人们为此而奋斗,当时的中国人有谁对此产生过怀疑呢?刘胡兰那么小,为了目标,把自己的头颅伸进了铡口;黄继光毫不犹豫的用血肉之躯挡了枪眼;懂存瑞的身体就是支撑炸药包的架子……
毛泽东先生,他向世人传播的是一种信仰,虽然是他杜撰出来的,可他用二万五千里的距离进行了播种,他种的田地获得了丰收,且颗粒饱满。他成功了,中国就如一轮晓日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信仰,有的拜日,有的拜火,有的拜树,有的拜泥……即使今天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神论的人,他的心中也会装上一个大大的神。每个人都有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内涵也许大相径庭,但形式却如出一辙。
比尔?盖茨,我也时髦的来谈他两句,他今年只有五十三岁,在中国文化中正值日中之时,他却辞去了微软公司总裁的职务,且把五百八十亿美元的资产全部捐献给了社会,这真是让中国人大开眼界的事情,同时也是让有信仰的人感到汗颜的事情。
还有伽莫夫——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今天的人懂科学不懂科学,总要说几句宇宙爆炸的理论。“曾对遗迹温度做出科学预言的伽莫夫,则以他特有的幽默来回应人们完美宇宙爆炸理论后的祝贺:‘我也许确实丢过一分钱,但当人在街上捡到一分钱时,我也不能说,那一定就是我丢的。’”这位谦逊的物理学家于一九六八年去世。他甚至没有得到他应该得的荣誉,但是他的名字却如科学史上所有的伟人一样永垂青史!
这些人真的让我们觉得那样惋惜,他们与真正的信仰只一纸之厚,却走向谬之千里的区域。
中国还有一位叫曹雪芹的人,他真的很伟大,在那么大的一部著作中只用了寥寥数语就把这个世界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难怪他笔下的贾宝玉会出世,会去作神仙,世上的一切对他是那么的缺少诱惑。
实际上人只要明白了这些浅显的道理,你就觉得这个顿亚也没有什么稀罕了。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隆起的土堆——有的曾富的嘴里流油,有的却贫的衣不蔽体;有的曾高官厚禄,有的却身为下贱;有的曾百岁耄耋,有的却懵懂夭折。如果不是最后的这一去处平衡他们的心,这个世界将会混乱不堪,灰飞烟灭。现在把纪念堂盖在天安门前与寄身山野村寨,对于一具躯体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奉劝人们应该多到坟地来走走,看看,感受感受,说不定你会得出一点于你的生命有益的东西。不要忌讳这个不祥的去处,因为你高兴不高兴都逃脱不了它对你的接纳!
……我走的太远了,我走的太久了。在离开的这些年里,父母曾为此奋斗过的这片红褐的土地搬迁的连鬼都没了,现在只能等到我们也和他们一样的时候,来这里宁静的歇息,长久的睡眠。
这里真是一个疲惫了、累了长休的天然所在,我将来就睡在父母的脚下,还依偎在老人的怀里,那样我才会永远感到温馨与踏实!
二
坟茔湾子上去就是鸡肠子梁,再走就是红沟脑,再走就是狼儿子崾岘……只要看看这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名,你就明白我的童年是在怎样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物质匮乏中度过的。不信,那些红褐的山山峁峁都是我在这里出没的明证——放羊、打柴、寻草、偷吃生产队里的洋芋还有小瓜……
在我的情感和思绪的深处,在六盘山北麓狭长川原的尽头和天际,在黄土与沙漠相间且互相竞争侵吞的辽阔的边陲,绵延横亘的就是这样一些起伏逶迤的红褐山脉。我不止一次的给我的读者描述过这样的环境。
红褐的山梁,红褐的沟壑,没有树,没有草,只有坚硬的石头和粗糙的沙粒,只有刺目的红褐——那种衰竭,天老地荒的红褐。初次步入这样环境的人只有一种感觉:这是一片死域,人迹罕至;没有一丝土,没有一滴水,没有可供粮食生长的土壤和可供人们活命的条件,谁迈进去必死无疑,除非伟大的造物者让他活。
这里没有过王朝建都繁衍,不承担支撑国家命运的责任;这里没有过部落驻足滞留,没有孕育出英雄。这里只有宗教神秘主义者寻觅石洞修炼,久居而磨砺;这里也可以放逐罪犯,使其煎熬,消蚀他们的凶残与奸诈。但无论什么样的活物滞留其间,除了幕天席地,以风为友,就只能听见自己清晰的足音、呼吸、心跳和脉涌的吼声;就只有孤独和苍凉,寂寞与无聊相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我走出大山的时候就是沿着这样一些弯弯曲曲的路走出的,今天我回来的时候还是从这样一些弯弯曲曲的路走进来。
……缺吃少穿在我们生存的那个时代,自然的象每个人出生的日子一样,孩子们三五成群想到偷生产队里的农作物几乎是定制。
偷什么呢?偷洋芋吧,在西北的山山峁峁,沟沟梁梁上到处种植。装在裤腿里没人搜到,逃到山沟里拣些柴火,把坷垃烧的红透了放进去,打碎坷垃埋了,上学的上学,放羊的放羊,到了傍晚聚集在一处分了吃。洋芋皮金黄金黄的,可醉人了。或偷些豌豆吧,在黄土山丘上修一个平平净净的陡坡,下面用土坎拦住,点燃豆蔓,就听见豆荚噼噼啪啪的炸裂,白里透黄的豌豆就顺着平坡滚下来,在土坎处拣,生的,半生不熟的,熟透的,顾不了那么多,抢着往嘴里喂,于是笑声从山头上一直滚落到沟底。或是偷瓜吧,不知道是谁提议的,于是得到了响应。实际上早就有人注意队上的瓜已经到了成熟的时候。下午放学,我们几个伙伴——都是堂哥,叔侄——不肯回家。已经打探好了生产队小瓜成熟的真实底细,选好路径,商量好下手的时间——季夏的月初,没有月光的晚上。看瓜的是我家爷爷,老人家本就老眼昏花,怕冷还在晚上生火。有个狗是拴住的,丢开了会伤人的。四个人一伙,把球衣领子用铁丝捆了,然后倒过来两人提着。剩下两人,一前一后。前面开路,挑软的香瓜摘,后面的防止爷爷追过来。断后的人选最精明强干、最机敏聪慧、最有应变能力的——堂哥就是最佳的人选。
偷瓜开始了,飞快的入地,飞快的寻找。狗开始叫了,爷爷听到了声音在扑火。爷爷跑来了,快到跟前了,但他还只是寻着影子追赶,后面堂哥忍不住把一个熟烂的香瓜擗到爷爷的脸上,小瓜的香气就在整个瓜田的空气里弥散。我们趁爷爷擦脸上瓜水的一瞬,全都逃到沟里去了。
第二天上学,路过瓜田,少不了要关心一下昨天的消息。于是装模作样的都去问爷爷讨瓜吃,爷爷讲着昨晚的遭遇,我们听的开心极了。尤其是堂哥还附和着说:“……就是,爷爷是多么善良的人,肯定会给我们很多瓜吃,怎么会偷呢,还伤害爷爷,要是让我们逮住了,非揍扁那帮坏小子不可。”然后我们都开怀的大笑,提高了嗓门儿!
果然在晚上,父亲先是把我给揍了,胶泥色的屁股越发的红紫,还不让吃晚饭——纵然那饭是照见影子的小米稀饭,或同样照见影子的大麦面糊糊。接着我们都到了队里的打谷场上开会,再次商量整治爷爷的计策……
实际上,后来我们的耳朵里才钻进大人们谈论的消息,咱们队就这几个孩子,如果是小孩犯错还能有谁呢?——难怪我们老不管做的多么严密,后来还是失败,我们都要怀疑队中的奸细了,才知道大人们的心计真是多,由此知道他们的狡猾,他们只要一动脑子就知道我们做什么了。虽然与爷爷斗智的过程我们常常失败,但是我们的肚子却从来都是填的饱饱的,这让我们成长的很快乐。
在生产队劳动是必不可少的事,寒假了,暑假了都要下地干活的,农民的儿子谁还不知道锹如何扛,镰如何握……
我睡在山坡草地上看太阳向西行走,听父亲的镰在嫩绿的草上割的剨剨的响……
头上正悬着一轮煞白煞白的太阳。我的身子就象涂了一层浓烈的胶漆粘稠而浊腻,垢渍而浊污;汗衫干痂凸起,又泛出一层白碱;又如一个甲壳虫;柔软的皮肤与衣服清晰的分离,感受着一种空洞的隔膜。祈盼着下一场雨,目光呆滞而冷漠,红肿而布满血丝。云是那样易散,没有一点怜悯与仁慈,刚才还有淘箩大的云朵,眼看着泛出灰青的颜色,有了雨的兆头,风就起了。从山的那边,秃秃的山坡上,还有崾岘口掠过来,云就四散开去。刚才那团团的灰青就化作缕缕丝丝,飘散又飘散。眼中的那点祈盼就没了,除了迷茫与惆怅。太阳又悬有低垂而沮丧的头顶,又是火辣辣的灼烤,刺目而晕眩。我睡着等父亲割够了一大捆,还有一小捆——那是我背的——寒木,寒木……唤过数十遍了才起来,父亲给我驮到背上,我就在前面开路。一小一大的两捆绿草就从山上悠悠的飘到沟底,再从沟底缓缓的浮上山梁。等再下到沟里的时候,我的小小的力气已经耗去了一大半,在一个悬崖边,终于不胜迎面的山风,脚下一滑向万丈的崖下坠去……我不知道,我父亲是用怎样的神力提到了我,把我和那小小的捆草放在了一个平台上……
回到家已是深夜,母亲很长时间不与父亲说一句话……
那天夜里,我独自一人坐在红褐的山坡上想着什么事情,星星像女妖一样的闪烁,充满了妩媚与诱惑。我被那最亮最远的吸引着,他那么高,那么远,孤单,明亮。真的,我在想,我是那么的喜欢,他如果知道,会不会肯为我落下来呢?
就这样的凝望,就这样的期待,也许期待的只是空虚与冷漠,我也满足于这样的空虚与冷漠。若有云梯爬上天,摘下的也许还是空虚与冷漠,我也肯!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他无限的爱怜与喜悦。我想把他摘下来,放在掌上,存在心头;让它温暖我的躯体,照亮我的前程。
我在暗暗的发誓——将来我一定要走出去……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了,我活着要比别人付出十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才有希望从目力所及的最远的那个崾岘——狼儿子出没的那个崾岘——走出去……
我咬紧了牙,为了父母,为了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我必须向前,我没有歇息的闲暇与可供选择的余地。
也就从那以后,父亲无论放羊,割草,收黄田再也没有叫过我一次,一直到他去世。
大概是要土地责任制了,宗教的氛围也宽松了,我才见父亲在礼完邦达拜后,去寻上一捆草,然后又把羊群与太阳一同送上山坡。傍晚他拖着疲惫身子跟着羊群与太阳一同走下山坡,还不忘在肩上架上一捆柴。他清静而又孤独,沉默而又寡言。他给人的感觉活着就是不停的工作,要用嘴表达的一切永远都是多余,他一如沉默寡言的泥土,静穆的山岭;不是他不善言辞,只是他不愿再为这个伪善、卑污的狗顿亚诉说什么情感了。
漫长的峥嵘岁月,铺满荆棘的坎坷路途,父亲教给我许多有益的东西,甚至包括他有益的言语。他说:“娃,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让它跑在你想法的前面。”
他还说:“娃,老百姓真苦,就像牛,一辈子吃的是粗糙的草料,套的是约束的格子,挨的是尖厉的鞭子,爬的是冗长的犁沟,活的是羸弱的生命,但永远难以改变的是骨子里生就的奴性。”
突然我觉得父亲像一个哲人,虽然他读书很少,可他的话竟如此蕴含深意,如一股激流激活了我久蜇的心,让我振奋而颤栗。
目睹父亲在世间的夹缝中挤着生存,用辉煌的生命勉强挣得半饥半饱、忍辱负重、步履蹒跚的日子,心灵深处就有一笔密度很大而沉甸甸的负荷。我今天性格的怪僻、孤独、不合群,大概更多地是缘于我父亲的基因,还有他为人之道的影响。
记得有一天,我看他慈善的面颊比原来似乎小了一圈,眼睛深凹,鼻梁陡峭,耳朵也显得薄而透亮,下颏凸出,老布汗衫的领子明显地松出一个大弧,甚而削削的锁骨也能明显的看到了……
我才想到他会不会病了……其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业已成了一个真正的国家公民了……
一九八七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莱麦丹月(伊历九月斋月)的阿哈勒主麻(本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穆斯林聚礼日)父亲复命归真,享年六十三岁。作为一个优秀穆斯林,莱麦丹的阿哈勒主麻这个日子与六十三岁这个年龄数就足以明证;作为西北门宦中一个优秀的穆斯林,二十四这个祭日就足以明证!
我父亲并没有享几天福,没有更多的分享我成长的快乐,他走的太早,太仓促!
父亲去世后的三年,我一蹶不振,我在黑暗中走过了人生中最悲苦的日子,没有谁能把我从那个阴霾漶漫的时日里唤回……我常常在梦幻中从他的身边走过,常常从泪水的梦魇中醒来,屋子里弥漫着疼痛,没有谁能像他那样让我的心境明丽……
从那时起我又立誓:我一辈子要活的像我父亲一样,我不会伤害任何一个好人……
可是我没有能够做到!
三
在深秋季节的少雨而多风的早晨,我在北方小县城的窝居里想着走过的路。没有什么让人深感陶醉的,因为什么都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该吃的都吃了,该喝的都喝了,该穿的都穿了,还有什么,还剩什么?实际上无论什么你有多爱,对你来说都是无穷无尽的奢望!儿女你很疼他们,他们会想到你吗?很多没有老人的人都很会劝人,如何如何的要善待老人。可是他的老人活的时候,你却从来也没有听他周围的人说起他就是当今世界的颍考叔。
我不是孝子,不能让老人的一切心事如愿。我在年轻时,也给老人翻过白眼,扭过脖子。在人生的路上也有无法弥补的遗憾——我母亲八十岁,快要临终了,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儿子,你对我真的很好。哎,可是我这一辈子竟然没有坐过一次火车。”我看定老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实际火车站就建在我家门口,整天轰轰的车鸣让人的头都炸裂了,可是我母亲却没有实践这个小小的愿望。实际等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一寸也不能挪动的人了。我当时想背她出去坐火车时,她却说你让我无常在车上吗?你让我在人世间出丑吗?我遵从她的话,让这件事成为我心中永久的遗憾。
现在每当火车从家门口出发时,我都要呆呆的站上很久很久,一种莫名的悲伤从心中泛起。只有车走的很远很远,没有了声息,我才从那个迷茫的梦中醒来。如果我早知道……可是啊,人呀——
人的心都是偏的,这是生理上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嘴上说对儿女一样疼爱,但总有偏袒。这种事要么你有很好的悟性感受,要么就等做了爸爸妈妈以后理解,不要过早的下结论,防止武断。
本来我母亲最疼的是我哥哥,这成为她的一块心病,甚至是畸形的。可是我妈不承认,我哥哥也许也不承认;当然没有人为这样的事去追问老人,作为兄弟更不能追问兄长了,“须贻同气之光,无伤手足之雅”吗!
后来好多人都给我说老人的偏心,但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而且在我看来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即老人疼的都是他在痛苦中抚养长大的,或是他心里感到懦弱或无能的,或家庭光阴(生活)比较拮据的——实际上哪怕在几个孩子中并不是这样,但老人就是这样定义的。即使这个孩子已经有了儿女,甚而至于有了孙子——只要老人还健在,那么无疑这是他的心病,而且是很畸形的一块心病!?
母亲疼爱我哥哥就是这个样子的。
一辈子她就把我哥哥的事当故经一样讲给我听,特别是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你哥哥是我在沙子淘出来的金子……她开始了。
……还是在生产队的时候,劳动非常紧张,我把你姐姐与你哥哥带到地里去挖苦苦菜。后来我们从山这边拔粮食拔过山那边去了,他俩就在原来的地里挖,等我们再回到山这边的时候,一个狼差点把你哥哥叼走了。我看到我母亲的手往前伸了一下,她的表情非常紧张。她说,我抛下粮食就向狼扑去,我不知道大声呼喊,我的嗓子里装满了棉花团一样东西噎着;我跑不前去,我的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那时候我想,狼啊,你要叼就叼走我的女儿,留下我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跑到你哥哥跟前的,我跪在了他的脚下……我听着听着,心里突然涌上一股疼痛,为了儿子竟然举意了女儿,我不知道我姐姐要知道这一幕心里该有多难过……
其实母亲还在世时,有一次我二姐来了,我说起了这一节,我二姐特别平静。她说,狼来了,我与你哥哥都不知道,看到妈抱着儿子哭的都快晕过去了,那时我就想,假如我知道狼来,我会主动迎上去,用我的小命换下我弟弟,为了我妈……
有多少人在为这个世界的儿子做牺牲,同时有多少人也体会了母亲为儿子的苦难的心,可是儿子究竟知道多少呢?
……你哥哥十二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我母亲有时间了,又给我讲——我抱了十几个昼夜,他眼睛不睁,饭不吃,水不喝。你父亲给他嘟着(大人把食物嚼烂喂到孩子嘴里)吃呢!我祈祷说:“主啊!你让我无常了,留下我的宝贝儿子吧,哪怕他是孤儿!”那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情感,怎样的一种心境,今天的人恐怕真的很难体味了?!她说着说着眼泪潸潸了,我笑着安慰母亲说:“到今天他不是还好好的吗!”
……哎,你不知道!哎,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母亲的这话我明白,她是说我不理解她的内心深处。母亲接着说:“你爷爷就只有他一个,你父亲来这个顿亚才二十七天,你奶奶又去世了。我那时也只有你哥哥一个,麻绳最易从细处断掉……”她说不下去了,只是抹眼泪……
母亲叙述说我也得过病,可是在我的生命如细麻绳快要断的时候,她则祈祷说:“主啊!你要是慈悯我就让他活下来,你要是不慈悯了,你就收了他……”我听了母亲的叙述,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在想,假如没有哥哥这根麻绳,你面对病魔缠身的我会有这样直率的心绪……可是我还是把泛在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谁让我生在了后面呢,我泄泄的走出了母亲的房间。
后来,每到我家有什么动荤的日子,母亲最先想到的就是我哥。她说:“你哥哥人口多,他又多病,你请一下他吧!”
即使我哥的日子过的比我宽裕,我还是尊奉母亲的话,总把他请来。等我哥吃好,再装上点提在手里的时候,我就看见母亲的脸上放着光彩,眉宇间弥漫着慈祥的笑容,似乎蜜糖就充溢了她的心胸!我知道,哪怕她嘴边没有粘一丝,只要我哥吃了,拿了,她也就心落到腔子里去了。
后来母亲走不动了,无法送我哥出大门了,她在自己的住房里,伸着瘦削的脖子,直看着我哥提着吃的离开我家……
自母亲去世后,我凡多多少少动荤时,总要先请我哥来。我知道即使我妈不在了,但她的灵魂也会非常高兴的注视着这一幕。
我有时回老家来了,或多或少的给我哥买点礼物,纵然我的景况很不如意,但是在我却完成着一个心愿。我总能感受到母亲曾征询我意见时的那双企盼的眼神,或许在某一处正在注视呢——你去看他吧……你把他请来吧……我甚至给妻说:“礼物很少,哪怕只是一星半点,只要哥哥接纳,母亲的灵魂都会高兴。黄土下母亲高兴,我们微不足道的尔麦力(善功)也会益济我们。”
母亲在临终时向我提了一个要求——儿子,你接纳你大姐来家里吧……我没有能够,那时我愤怒的如一头狮子……我真的很蠢,我后悔了……
我知道,终有一天,我会睡在父母的身边或脚下,这是肯定的,是不可能回避的事实。我石破天惊的懂得了伟大造物主的刑法是严厉的,伟大造物主的刑法是严厉的……这是我最最恐惧的!
坟茔湾子的这棵柳树可以作证——它曾见证过这里的苍凉与悲壮,高尚与卑贱,它曾俯视过我母亲的身影走过,它曾权威的诠释过我母亲的为人与行为,它是一部无字备忘录,是一架无镜摄像机。——今天我跪在父母的丘墓前,心境是这样的复杂而不安,我茅塞洞开般的想到——安拉的刑法是严厉的,安拉的刑法是严厉的,我们都将接受最终的审判!
对此我深信不疑,对此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
四
一抹阳光穿透记忆,往事如诗如歌。我站在鸡肠子梁上,遥望着弯弯曲曲的狼儿子崾岘,我曾经就是从那里走出这些大山的。我像任何一个走过生活路的人一样,在定长的生活半径里急骤的奔波,结果绕了一圈又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现在我就真切的跪在父母的丘墓前,心里盛着很多说不出来的东西……
我想对着父母沉默的坟堆,对着无言的山野说出我的心思——
可是我无言!
在孩童的最初,父母亲不知道多少次的唠叨过他们的意愿,想把我培养成一个穆斯林的阿林,最少要在我们这个家族中成长为一位阿訇(教长,或有伊斯兰知识的人),但是命运却阴差阳错的让我读完了大学,成了一个社会工作者。其实那个时代也只能这样,虽然父亲教我《忠诚章》时,我学的很快,那些蝌蚪文字让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辨的出。我也曾想着改变与同伙们老去队上的瓜田、洋芋地做老鼠、狐狸的勾当。每看到年轻的阿訇在成群结队的乡亲簇拥中请去作客,心里就有一种如吃了蜜饯一样甜甜的感觉,我爱那种感觉。如果有一天如阿訇一样,或者快快的长上胡子,坐在阿訇的身旁,我就能饱饱的吃一顿了,但这如流星般飞逝的情景只那么一闪,一切教门的光亮就散失殆尽了。我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有的宗教都成了四旧,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是牛鬼蛇神、地富反坏。人们像躲避瘟疫般惟恐不及,哪有无端的把头伸到胶锅里去的。
于是,我在社会学校里一天挥汗如雨的与同龄的孩子比着高下,终于有一天父亲送我出关般地走出了大山……
哎,人的命运呀,谁能料想呢——
当初那样执着的走出,也许就是今天这样沉静的归回。
我在想:父母亲辛辛苦苦的培养了我,寄我于厚望,希望我能出人头地,能有出息,这些不单是他们,就是那些善良的同事也在不停的劝勉——先找个高点的位置,或多或少的捞点油水;再熬几年就能拿到百分之百的工资了:熬吧!一辈子生在底层活在底层,对自己总算有个好交待。
是啊!我就是怕一生没有个好交待,我才放弃了工作,我觉得这是伟大造物主对我的疼慈。那或多或少的油水捞不到也就罢了,要是真的捞到了,将来我站在属于我永恒不变的位置,我将如何交待的清呀?还有那百分之百的我的想望,我的想望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手呢?我什么时候才能满足呢?我来到这个世界什么工作都做了,虽不完美,但并不很失败,就是没有与伟大的造物主签订一个永生的合同,我不知道那一天也像我的父母亲一样宁静的睡在这里?想想老人疼我的情状,也就是最终让我有个好归宿,七十万年的火狱谁想滚落下去啊!
我选择了自由——那种全身心没有任何干扰的自由,轻松的就像除了安拉没人过问一般!
本来父母是过问的人,但长眠于地下了;妻是一个唯命是听的人,她辛苦的一生只为我家四代人过活的好;孩子们还没有成长出一种过问老人的资格。如果让今天我们民族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上流与精英们成为我们的表率与先锋,我真不知道我们将会走向何方?
我选择了放弃,我觉得我在犯罪。现在我们这个民族的上流们与精英们做事连党国的官僚都不如。党国的官僚在用国家的钱财时,常常还要显出一副害羞的样子,坐国家的车还要寻找一千个能让别人体谅的理由,否则就是不原则。而我们民族的上流与精英们打着宗教的旗帜,干着掠钱、沽名、渔利的勾当,而且是赤裸裸的,一点害羞的样子都不用装。
有一句话真是太经典了,用来描绘他们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两只馁狼放进羊群,对羊群的破坏远不及一个沽名钓誉、贪婪钱财的人对教门的破坏!
崇拜金银和华丽服装的人亏折了,如果他得到,他就满意;如果他得不到,他就沮丧!
其实谁也不能否定金钱对人的诱惑,那是一种让人窒息的魅力。无论你崇高还是卑陋,无论你富足还是窘迫,谁会对着黄灿灿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和大把大把的钞票无动于衷呢?不是我在危言耸听,而是我们被这样的环境围剿。
或许有人会诘责:我们的圣人就不爱钱——他说:有伍候德山一样大的一堆黄金放在我身边三天,我也不喜欢拥有其中一个金币。除非为了偿还债务而留下的一点。是啊,他是圣人,可我们是凡人……。当然也还会有人继续诘责——中国人的祖先以自己非常含蓄的方式也曾向我们昭示过,人不会嗜财如命。《世说新语》中就记载管宁、华歆二同学在菜园里锄菜时发现了块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后人还批判华歆爱慕虚荣。但他们的确不爱金子,可他们早就死了,不知深埋在哪里了,今天的人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吗?
今天的人,尤其是我们民族的上流们与精英们,他们首先是要出国,这是必须的,常常的……没有理由,不需要理由。他们哪一个扪心自问——伟大的造物主啊,我这次出去完全是为您的事业,为宗教的事业,您是见证者——无论是“公民”,还是“私民”都在往外走,偕同妻子、儿女!
他们还要有车,要有房子,要有存折,还要考虑大舅子、小舅子、大姨子、小姨子、尊夫人、如夫人,还有小皇帝、小公主……,有时还要考虑弄不弄个女秘书,还有二奶……考虑的人实在还不止这些,还有亲戚、朋友、学生……,还有……还有……
我说不过来的那些因素,像雪片在这个世上纷纷扬扬的飞舞,再能不能扪心自问——我们坐车是为了教门,我们的房子、存折、大舅子、小姨子都是为了教门?名呀、利呀——在这些事情中我也是参与者,也是一个同伙,不折不扣的!我们常常认为今天的穆斯林没有素质,不台格瓦(虔诚),我们说这话的时候总抱着一种心态——除了自己,全是伟大造物主的公敌。
——哂哂,哂哂——
用现时年轻人的一句很时髦的话说:谁也不是谁的谁。我们谁是这个世界的一把尺子?谁是人类奉为道德与行为的一个标准?稍有伊斯兰常识的人都心知肚明,那个尺子是早就存在的,看我们衡量不衡量自我,完美不完美自己。有没有信仰,虔诚不虔诚,那是我们与伟大造物主之间的事,不是与哪个人之间的事,将来要面对的是造物主而不是人,谁说服了造物主,他就是天堂的居民;谁说服不了造物主,他就是火狱的烧柴。我们凭什么老指责别人?——你们怎么只说你们做不到的呢,你们怎么只说你们做不到的呢!
还是自私的想想自己吧!
说客气点,不过都是一群伊斯兰的伪学者、假哲人;说丑了,不过是一伙毁坏先辈名誉名声的败家子,一帮鸡鸣狗盗之雄耳。每个人的情感、思想都在不停的压迫着别人,侵略着别人。这真是受新帝国主义豢养的宗教,就像美国佬一样的霸道!
我离开了工作岗位,离开了心爱的事业,我也下了一个暧昧的决心做了抉择!
现在我突然觉得,这些自命不凡的上流与精英们谁都嘴上从来没有说过心里的话!
当我跪在父母的丘墓前,我真的无话可说了,我还要说什么呀!
在这里,谁还会像我一样在生活中走了这么远、这么久之后,再一次回到了心灵的港湾,回到养我育我的儿时的摇篮聆听山风的韵律,飞鸟的歌唱,还有花草树木的私语呢?谁还能在生活的平淡与无奇里来向深厚的大地诉说衷肠呢?谁还能来到宁静的睡在墓穴中父母的丘墓前向可敬的老人问好,并给他们诉说自己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呢?
请不要忘了底层,看看你的故乡——生你养你的故土吧——看看那些山脊上扶着老犁,赤着脚丫,终年数着牛蹄窝窝的你的兄长与子侄吧!他们弓一样的脊背,毂一样的身子,向你阐述着生活的艰辛与凄苦。看看那些赶着羊群与太阳一同升上山坡,又一同落下山沟的流着鼻涕的娃娃吧!他们小小的脑袋里只有一种逻辑,一个真理——放羊,挣钱,娶媳妇,生孩子——孩子再放羊,再挣钱,再娶媳妇,再生孩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矢志不渝的守候着祖先留下的这一千真万确的定律。看看那些不安于命运摆布,以为走进城里就等于迈进天堂的打工的我的弟弟与妹妹们,当我落魄的回来的时候,我就是他们的前车,他们就是我的覆辙。
蓦地,我发现我们这些生在幸福中而活的不幸福的人,这些拥有知识财富而精神追求倒闭的人,无知之极,渺小之极,肤浅之极,轻狂之极,悖逆之极,健忘之极。当四川发生特大地震,“死亡的消息从大地的纵深处慢慢的膨胀,裹挟着人们交付自由;地狱横卧在我们的脚下,威逼一切生命临难就犯。毁灭的气息在汶川的山头、沟壑中掠过,黑色的灾难从川塬河流里浮起。”我们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我们就痛不欲生,或集体自焚。当北京奥运举办成功,我们确信人民富足的流油,祖国无比昌盛,只要一抬脚板就会迈出国门,就会在顿亚上成为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于是大街小巷,旌旗飞扬;家家户户,炮声隆隆……可是我的父亲一样的男人,我的母亲一样的女人,你却只能看到他们一生忙碌的背影,这些百年一遇的事情,这些天大的事情,究竟会触动他们怎样的神经,波及他们怎样的生活,影响他们怎样的命运?红沟脑里,他们快成熟的洋芋还没有刨挖,深秋的寒冷威逼着不许怠慢;鸡肠子梁上稀秕的谷子还没有收割,冻蔫了就没了人们这一年依赖的周粟,牛羊这一年依赖的草料。公家不管你愿不愿意,听与不听,断水,断电,炸路。封山禁牧——这是国策,国策,国策!只需一亩八分的水田就要让他们搬出祖祖辈辈生存的土地,必须放弃他们的栖息之所与放逐之地。他们简单的头脑,一根筋的思想,还有疲惫了一天的身子,抛在布满灰土的炕头上,吃着烤焦的洋芋,又如何谈论,辘辘饥肠任凭他们怎样谈论这些天大的、百年一遇的事情?
罗曼?罗兰说:当你想望遥远的东西时,不至于对眼前狭小生活中的恩怨去计较。我们虽然有时不免糊涂,但不要忘记在该醒时清醒。虽然我们有时也犯错误,但在该悔悟的时候要不忘悔悟。有时我们妒嫉,但别忘了人生总有波折。有时我们抱怨,但要明白我们的趋向。这样,我们才可以在糊涂和妒嫉时保持适度的清醒。
“快马先死,宝刀先钝,良木先伐。”同时我感到了这个不义的世界哪里会有公平、公道和公正?
那山头上我的叔伯子侄,那庭院里我的婶娘姊妹!——我还怎样说出我心中那句埋藏太深太久的话语。
突然我觉得我亏欠伟大造物主的太多太多,我冀希着有一个偿还累累债务的机会……
在漂泊的日子,无论是在有树有水的那个让人想来就孤独的滇南山野,还是红褐刺目、寸草不生的陇西川原,我走着我人生的路。我的思绪是那样的冗长、沉静,一路走着我想了很多,我的心也很痛,我的情感与思想就像飞升的气球,在不断的上升、腾飞、翼鼓。可是不久就炸破了,从很高很高的空中坠落,失去了位置。我很傻很傻的仰头看着天空,总以为那个气球会在空中的某一位置停留,或被什么东西挂住。
可是一切都是照样滑落了!
迄今我还会想起我的劳作,我的辛苦;这不是吝啬,而是一种远念;那种心里牵挂、惦念,时时萦绕,时时纠缠,难以名状,难以理喻。
去而复返,我又回到了陇西的黄土高原,回到了西海固——这是我的故乡,我的流放之地与栖息之所!同时也是我的二位老人立命又安身的所在,我在努力的靠近他们,还有他们曾经追逐的精神天空!
-9-30
哈尔滨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手术需要多少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