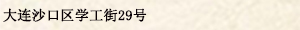兄弟,你在他乡还好吗谨以此文纪念早逝
今天是腊月二十七,再过两天就是农历的春节了。东涡河大堤两旁的庄户人家业已忙碌起来,煎肉圆、蒸包子、贴春联,都在忙着准备过年的活了。空气中弥漫着煎肉圆的味道,还有那提前响起的一星半点的爆竹声,让这座村庄浸润在快要过年的喜庆气氛中。
一条不太平坦且狭长的田间泥泞小道,向着西北方向弯曲延伸过去。一轮残阳孤独地悬在西边的天际间,冷冷的,感觉不到一丝温暖。我带着柯儿,还有小侄子毛毛,默默地沿着小路前行。沿途很静,除了瑟瑟的风声,就是两个小家伙偶尔交流的嘀咕声。大约半个钟头的光景,我们到了墓地。一座孤坟,四周是弥望的麦田,很是空旷。远远望去,是广袤的褐色土地;近近细看,才能看到黛绿的细微麦苗,他们在凛冽的北风中蜷缩着。墓地东边是一条南北流向的小河,河两岸的斜坡上尽是枯黄的杂草。不远处,一棵光秃秃的榆树,老枝横丫,像步入耄耋的老人的手,在风中颤巍着。不知何时,一只乌鹊从河对岸的麦田沟漕中倏然出现,贴着河道中央的水面向北无声地飞去。
此刻,这里显得愈发的孤寂,时间似乎凝滞,让我的心郁郁难受。这里,就在这阡陌荒野,就在这一抔黄土之下,静静的躺着我亲爱的兄弟——小马。小马,是我老姨家的儿子,是我姨表亲的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因为生肖属马,所以大家从小就叫他“小马”。小马,小我三岁,姨表亲的兄弟姐妹当中因与我年纪最接近,所以玩得也近乎。
看着孤零的坟丘,没有墓碑,我的眼中禁不住噙满泪水,我的思绪也飞越到了四年前的今天。那天上午,我在单位办公室突然接到我姨姐夫的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姨姐夫低沉的声音,说小马走了。开始以为两口子闹别扭小马离家出走的呢,我还说走就走了呗!但姨姐夫解释说,小马死了,开车出事故死了!虽然手机信号不好,听得不是太清楚,但我清楚地听见了“死了”!当时,我的头脑“嗡”的一声,心头一凛。不敢相信,绝对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失声哭了。同事突然见到如此状况,急忙关切地问发生什么事了。我说,我兄弟死啦!我兄弟死啦!!
这一天是腊月二十七,再过两天就是农历的春节了。
等我赶到老姨家,院子里,大屋里,小屋里,里里外外都站满了人。早就听见小马妻子呼天喊地的凄惨哭声。她头发凌乱,捶胸顿足,泪流满面,在场许多人都感动得落泪了。我挤到小马兄弟的遗体前。小马静静地躺在棺板上,棺板有点大,使得本来就身材瘦小的他显得更加的瘦小。瘦削的脸庞,面色苍白灰暗,眼窝些许凹陷,嘴唇发紫。可以想象得出,他出事故时死得很痛苦。西房间里,老姨倚靠着床背,面无表情,泪痕斑斑。她一双眼睛红肿着,布满血丝;口里含糊着,不停重复唠叨着小马的名字。小厨房里,老姨夫默默地坐在靠门的小板凳上,头发蓬乱,还沾着灰。他锁着眉头,目光迟滞,只是一声一声地叹息。
后来听说小马出事故的情况是这样的。腊月二十七一大早,小马冒着刺骨的寒风就驾驶着自己的三轮摩托车出门了。因为承接了正月初二的一笔家宴生意,他要去家北边的一个村子借家宴用的彩棚及钢架。在返回的路上,当车开到东涡河大堤两村交界的弯道处,可能由于车速过快,来不及打方向盘,连人带车一下子翻落到大堤的斜坡上。车卡在一棵树干上,小马的身体被牢牢地压在车下,动弹不得。此处位于两村交界,平日里就少有人往,加之此刻尚早,天气寒冷,更是无人问津了。可以想象,当时的小马兄弟是多么的绝望无助!多么的痛苦难耐!他是多么的希望再看上一眼自己年迈的父母,再亲抚一下自己年幼的儿女,再拥抱一下自己深爱的妻子!
小马出殡的那个凌晨,我去送他了。当天夜里在床上迷糊了几个小时,没怎么睡着。我的体质本也不好,加之这突来的变故,竟感了风寒,喉咙疼,还有点咳嗽。母亲担心我,但我坚持要去,因为我要送我兄弟最后一程。出发去汞沟殡仪馆之前,母亲特意给我加了一件棉衣外套。
凌晨四点多,当小马兄弟被推进殡仪馆火红的焚烧炉时,送他的亲人们再一次痛哭涕零。从此,再也看不见我的好兄弟了,真的永别了!从此,兄弟你只能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的脑海里!
当小马兄弟的骨灰送到墓地安葬时,天色还没亮。黑夜,黑得怕人,没有星月;墓地,静得怕人,少有声音。除了凛凛的风声,就是仵作们挖坑掘土的声音,其他人在静静地候着。侄儿毛毛手里的电筒发着微弱的灯光,不时地在祭品、墓坑、麦田和送别的亲人身上飘忽着。当棺木下葬时,鞭炮响起,僧人念经,操度亡灵平安踏上黄泉路。当最后一抔黄土覆盖其上时,凄凉的唢呐声穿透漫漫漆黑夜色,飘得很远,很远。
丧事结束后,我和妻子告别老姨一家。临别前,我安慰老姨二老节哀顺变,日子再苦还是要过下去的。看着刚上小学的孙子毛毛,还有那咿呀学语的小孙女,老姨父用他那长满老茧极是粗糙的双手紧紧地握住我,眼中噙着泪水和忧伤。小马的妻子也极是憔悴,拉着我母亲的手坚定地说,她永不嫁人,要把两个孩子养大成人。
今天,是小马兄弟离开我们四周年的日子。我静静地站在孤零零的坟丘前,思绪又带着我回到了兄弟俩过去相处的欢乐时光。
儿时的印象中,老姨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高高的土墩之上。那土墩上住着几户智姓的人家,老姨父也姓智,我姑且称之为“智家墩”吧!每到暑寒假,这里就成了我们姨兄弟们开心度假的必到之处。智家墩后面的坡下,是一块块整齐划一的菜畦,其中要数我老姨家的菜地长得最好。菜地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瓜果,有青椒、茄子、黄瓜、丝瓜、冬瓜、香瓜、豆荚、韭菜、菠菜、甜菜等等,说也说不清,反正要什么有什么!尿子哥,是我五姨家的,大我三岁,小名尿(读音niao,去声)子。他经常带着小马和我到墩下“巡视”一番。番茄刚变红一点,摘了;香瓜咬一口没熟,扔了;黄瓜吃一口还涩,踩了。我们这帮小土匪,气得老姨哭笑不得,但她还是把最好吃的留给我们。老姨家房子东边是一条小河,河水一年四季都碧清碧清的,可以看到底。每到夏天,我们兄弟三人就扛着木澡盆下河嬉水,捡螺蛳,摸河蚌,掏螃蟹。老姨家房子东边的河堤上,长了一棵老桃树。夏天枝叶繁茂,树荫下覆,纤藤细草,景致怡人,也是纳凉的好地方。一到秋天,枝头上结满了桃子,个状不大,类似野桃,但脆崩甘甜。尿子哥爬到树上摘,我和小马在树下抢着,挣着,闹腾着。兄弟们欢乐开心的笑声,和着枝头鸟儿的叽喳声,传出数里之外。
这样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已至少年。这时候,老姨家已经从智家墩搬到村里的新居民点了。这一年夏天,小马兄弟刚刚初中毕业,而我也才参加完高考。等待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漫长而焦急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录取通知书,所以,为了避开左邻右舍以及大人们不停的唠叨,我就躲在老姨家不回去。每天的家务活,我和小马分工合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烧火来我站锅,他掏锅膛我倒灰,他扫地来我抹桌,他盛饭来我来吃。呵呵!说实话,重一点脏一点的活,都被我兄弟抢着干了。到了晚上,小马为了纳凉在屋外搭上一张竹床。兄弟俩躺在上面看月亮,辨北斗,讲故事,吹牛皮。一天下午,天气异常闷热,老姨家的小鱼塘因缺氧而翻塘。正当我和老姨父在鱼塘抢捕时,小马蹬着自行车风风火火地赶来了。老远就看到他面露喜色,嘴里嚷嚷着:“哥哥,哥哥!录取通知书到啦!录取通知书到啦!”那最后的“啦”字声调拉得很长。我高兴极了,扔下渔具,撒腿就和小马回家去了。
后来,小马没继续上学,独自一人去了常州跟着师傅学习扎牌亭(祭祀用的纸制品)。小马很聪明,学一行,会一行,会一行,精一行。有一次,尿子哥、小马和我兄弟仨又遇到头,就戏谑小马,喊他“小和尚”。十七岁的小马兄弟嫌难听,急得要哭,回去逼着老姨老姨夫两人同意改行学厨艺。很快,小马学会了一手好厨艺,在离家不远的镇上凤祥酒店做了掌勺厨师。再后来,经人介绍找了老婆成了家,生下儿子毛毛。当积累了一定经验和人脉关系后,小马夫妇自己办起了“小马家宴”。因为价廉物美,服务周到,加之小马待人热情善良,从不和顾客斤斤计较,所以,很快生意应接不暇,兴旺起来。后又添了小女儿,一家六口祖孙三代相处和睦,其乐融融。
十年前,我家从乡下搬到城里后,小马及老姨夫妇经常进城送些油米酱辣、瓜果蔬菜,还有美味的野生鱼虾。我也经常趁周末或者假期,带着全家老小下乡去小马家玩。傍晚时分,我跟着小马去放丫子(一种七字形的捕鱼笼具),第二天早上竟能收到不少野生黄鳝。有时候,小马撑船,带我去偏僻的河塘渠沟捕鱼,不长时间就会捕到好多鱼虾。每次到了老姨家,我除了尽情地享受一顿绿色、天然、野生的美味,临行前小马兄弟还给我捎上点。
可谁曾想到,四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兄弟这么年轻,就如此早早地撒手人寰。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看着孤零的坟丘,没有墓碑,我擦拭着眼角的泪水。墓前,侄儿毛毛和柯儿跪着烧纸。纸灰在墓前随风盘旋,飘到麦田,飘向天空。不知何时,那只乌鹊又回来了,绕树三匝,落脚枝头,悄无声息,默视这里的一切。它也许是我小马兄弟派来的。我想问它,我兄弟在他乡过得还好吗?他想念亲人们吗?他知道父母亲一直思念着他吗?他知道亲人们一直忘不了他吗?小马兄弟,你知道吗?老姨父他老俩口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最痛苦也是最最思念你的人。因为,血脉里流淌的亲情,是永远都无法割舍的,但他人呢?既然不能坚守,就不要轻易许诺。这倒是应了一句古语“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小马兄弟,今天是腊月二十七,也是你的忌日。快过年了,哥哥祝你在他乡,一切安好!
鐧界櫆椋庡尰闄㈡矆闃冲摢瀹跺ソ灏忓鐧界櫆椋庡ソ涓嶅ソ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