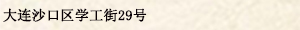世上最鲜美的味道用饭盒舀嫩江水,加点盐
叙旧
谈天
取景
采风
社戏
我儿时的记忆,那些堪称经典的走街串巷吆喝声,常常在梦乡回荡。透着故土浓浓的民俗风味。“磨剪子喽,戗菜刀!”“冰棍儿三分五分!”“冰棍儿糖葫芦!”“劁猪喽!”那些吆喝口音,南腔北调,悠长醇绵。常有童稚的学舌声跟着和。那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重滑音上扬下顿腔调,常是模仿戏弄的笑点。
小孩子家跟大人逛简陋古旧,青砖灰色基调,原汁原味的中式街衢,熏染那些老字号店铺的传承风味内蕴。现在想着都挺奢侈的。那已是一个永远飘散的梦境。
能吃上五分的冰棍儿,就有浓浓的牛奶香味了。挺美味享受的感觉。卖冰棍儿的,多是扎白围裙的老大妈。推辆两大轮或四小轮的手推车。四四方方的大冰棍儿箱刷成蓝色。箱内四壁用绵絮隔热保冷。三分的就是煞白的冷冻糖精水。五分的就有奶黄色。冰糕一毛一勺,纯牛奶做的。奶香味道浓郁。坐在凉亭子里享用冰糕,那绝对是有钱人。
我家住在劳动湖边的一趟红砖房把头,紧挨着湖。上街要从湖中间的木结构小桥穿过。桥两边都是清澈的湖水,深不见底。经过回民小学,上坡就是古驿栈----西栈。是一片回民聚居区。
除了十九世纪末上世纪初留下的很讲究的中式青砖瓦舍,正房厢房雕梁画栋严然的红漆大门庭院。多是土坯砌垒的泥房屋泥院墙。
户户内皆养奶牛羊及狼犬护院。一到春秋两季,就有牧人带着狼犬,推着两轮大车,赶着成群的奶牛羊经小桥,从我家后山经过,奔西头嫩江畔放牧。嫩江共四道泾流,中间两座孤岛草肥水美,用船把牛羊运到岛上,就不管了。牧人就去打草。
到夕阳坠落的傍晚,拉着满满一大车足有四五米高的草垛,赶着奶头胀鼓鼓的牛羊,带着狼犬,慢悠悠的返回家。
西栈有个著名的古清真寺。庙塔尖那个圆葫芦状的金顶,据说是纯金铸成。央视在介绍该市风景名胜时,还特意渲染了一笔。
我夏日喜欢泡在湖水里,无师自通的狗刨,扎猛子,仰躺湖面漂浮。钓鱼捞虾。赶着上小学一年级,游泳教练刘云恒(闫明,黄小敏的教练)到龙沙小学选苗子,选中了腿长,胳膊长,手掌大,脚掌大,水性好的我。
冬天湖面冻冰层刚能禁住人,就带斧子出溜溜尥上去,冰层下因缺氧,浮一层翻白肚皮的大鲤子大鲫瓜子。凿开冰层,唾手可得。但也冒险。冰层毕竟太薄了。
我家居住的院落是一所学校的家属区。除教职员外,各色人等都有。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已没工作的秃头锃亮的“右派”。他毕业于吉林大学。放猪娃出身。有侍无恐,成了戴帽监督劳动改造“右派”。小孩子家成帮跟在他身后嚷嚷:“秃子秃子向前看,前面就是电影院,今天演的《刘胡兰》,明天演的《赵一曼》,就是不让秃子看,秃子一看就跑电。”
常常气得他脸色青紫,脖筋肿胀。他一家大小六七口人,都靠当小学老师的老婆生活。
有个秃顶,络腮胡子诗人,遇见就会训斥顽童一顿。他那亮晶晶的大眼珠子一横棱,没等吓骂,小孩子就给吓堆儿绥了。
此外还有走街串巷,挑挑子,给人剃头的老头。捡煤胡的老太太。食堂作饭的老厨师等等。
剃头挑子老田头,好钓鱼。浮漂杆线和铃当甩线一并用。到嫩江河套,江岔子,回水漩涡,钓夜鱼,一宿就能钓个几十上百斤。可惜了:年纪大,驮不动。只捡鱼肉好吃鲜靓的往家驮。余皆再扔江里。那可都是现今早已绝种的野鱼啊。
老田头戴副眼镜,头上三毛式的稀疏几根白毛。斯斯文文的脸面总浮着笑意。闪亮的目光却深邃幽远。对小孩尤其和善,软语慈眉哄逗。听说有些文化的。床头古书砖头厚一本。教职员女儿女婿都不大看得懂。不知怎么就剃上头了。
捡煤胡的老两口却都是粗人。老头对襟黑绵袄,腰里扎着麻绳子。一头白发。一张核桃模样的脸目。老太也差不多。
捡煤胡,也稍带柈子,煤块,凡稍能用之物皆在“捡”之列。出身苦大仇深,腰杆子不软。一般都看不见的。北方传统风俗谙熟:包饺子,蒸黏豆包,淹酸菜,灌大肥肠。扒火炕,砌炉灶,通烟筒。常常向移民传授技艺。邻里关系浑和。老头是学校的更夫。
其子女皆脱盲:老大在外交部。老二亦在京谋事。老三警察等等。
老厨师好抿口小酒。好养画眉。那清脆空灵,千回百转的啼鸣至今仍有印象。听说他以前是当警察的。有老伴儿,无子女。我一度是这老两口跑腿学舌的当差。打酱油醋,打散装白酒,都是我跑校外小铺去给采买。
这三人对我都有影响:我常跟老田头去钓鱼。跟老某头去捡煤胡。到老厨师的小院,看他饲养画眉。我还跟牧人去放过牛羊。那是幼儿园毕业,还未升小学的空当。疯玩的就一天天不着家的野孩子。
后来,我按学区入读公园路小学。一年后,转入市里最好的龙沙小学就读。
我家随父亲的工作调转,搬迁到“歌舞团”大四合院。这院里再没有那样形形色色的人喽。清一色的老师及家属。都是斯斯文文,客客气气的一种氛围。随着年级的升高,家长开始告诫孩子:考重点中学!考不上就得入读职校。谁谁的孩子没考上重点,读了职校。那口气,那神色,仿佛大祸临头。不过,这种紧张气氛,随文革到来而烟消云散。升中学根本不用考了。也再没什么重点不重点了。重点的,都成了文革火力集中轰炸扫射的标靶。小孩子家可是解除了紧箍咒一般,欢呼雀跃。全然没有察觉到大人脸色越来越难看。
我们一帮小嘎豆子,甭说课余了,到校就是所谓革命。斗老师,斗校长,参加派别。课早就没影了。打群架,大串联,还走丢了学生。家长哭天抹泪的向学生集体诉说,天寒地冻,孩子还是单衣单裤。也不知最终找到没。
我记得书记叫吴瑶,校长叫鲍革非。
书记是上海人。穿着精致讲究。骑一辆天蓝色26坤车.
鲍校长四十不到。蓝色尼子衣裤笔挺。裤线可切西瓜。威严脸面。眼神凌厉。数学教得颇有名气。
鲍校长站在主楼门前的台阶中间,弓腰屈体,胸挂名字打黑叉的大牌子,接受高年级学生批斗。
每班派一个代表,站在位于台阶上的麦克前,宣读揭批稿。振臂高呼打倒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总代表鲍革非的口号。
她外甥候捷跟我同班。关系很黏糊,他后来在铁路当工人。候捷的爸是二厂工程师。家里铺红地毯。进门要脱鞋的。候的姐姐叫候丽,有印象。现在也六十多岁了。
还有个叫王阳的同学。后来上东北工学院读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在市府法划处耍笔杆子。
赵春生后来在建行。
同桌张爱齐在市税务局当文秘。
恢复高考后上学的,就我一人。
其余天涯海角,四散漂零,不知所踪。多数都不如意吧。
出了校门就成帮结伙奔浏园,葫芦头江边撒野,钓鱼,捞虾,游泳。整日价泡着不着家。皮肤晒得黝黑。
游泳,我在那帮混世魔王,祸根孽胎坯子里,是个头儿。以敢冒险,游得快,游得远出名。不只一次救过人。
说来出奇:凡家长开明,鼓励孩子游泳的,管保安全。从不出事。
凡家长怕孩子淹着溺着的,严禁孩子去江边野浴的,多半肯定会出事。
小孩子家憋不住,大热天,禁不起嫩江的诱惑,同伴的拐带撺掇,背着大人,偷偷摸摸溜到江边下水。
呜乎哀哉!有一家,让溺死鬼号上了,兄弟三人先后溺死。中间只隔一年。
那时,嫩江水可直接饮用。我们中午带两窝窝头,就江水就吃下去了。游泳时特别耗费体力的。肚子一游就空空荡荡。就用饭盒舀江水,加点盐,煮刚钓的鱼虾。那味道之鲜美,久违了。
柴是现搂的。可煨烧土豆充饥解馋。那层烤焦糊的土豆皮,甭提多香了。土豆是就近现起的。
靠江边,有一大片果林,叫园艺试验站。那也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宝地。那果树用力一摇,脑袋都能砸出包来。用半截袖一兜,撒鸭子就尥。常吃撑得自退江山。
有回,几个顽童爬到树上够果摘梨。园艺师付站在树下轻轻问,摘够了吗?不敢喊。说是怕摔着扎着担不起责任。
后来大人听说,狠狠训斥一顿,人小鬼大,也渐有羞耻之心。不再顽劣了。
嫩江共四道泾流。中间三座青草一人深的岛屿。我八九岁就能游过四道江。游上岛屿,有种征服自然的成就感。岛屿远离尘嚣,人迹罕至。鹤鹭鸭雁近在咫尺。起起落落,羽翅圣洁,长啼细语。那氛围,孩童也体会到解脱的静谧舒放。
游过四道江,就是无边无际的碧绿西瓜地。交五分或一毛钱,给窝棚里看守西瓜地的白胡子老翁,就可够呛。走时还可稍上两三个大西瓜,作救生浮漂。
能裸身游过四道江的,毕竟是极少数。
土泳狗刨,即毛式游法,又慢又累。紧着刨挠,也不怎么动地方。遇有漩涡激流,根本冲不出去,靠不上彼岸。
救生圈又累赘,又没面子。
所以登上四道江彼岸,常怀:风烈烈,剑在手,问天下谁是英雄的豪气。
挑选西瓜的门道,就是那阵儿清的。
叫一看,二拍。
先挑个大,饱满。个小,有疤瘌疖子不成。再看色泽。老绿油亮准差不离。暗绿无光,是死秧瓜,或困熟的。红瓤但不甜。更不沙。囊了耨了。
拍是听动静。清脆响亮不熟。沉闷空音准熟。越沉闷越是沙瓤爽口。还需捏瓜皮,以防熟大劲耨了。
香瓜只需闻瓜蒂的香味就能选中。
摸蛤蚧。几斤沉,半个脸盆底大的蛤蚧,深深嵌进没脖深水的沙底里。外露一条小边儿。用脚在沙底上平蹚。拨拉不动的准是。憋口气,扎下去,双手紧紧抠住蛤蚧,以防被激流冲走。错失蛤蚧。扒掉两边的泥沙,抱着就浮出水面。
两三米深水沙底,蛤蚧更大。扎下水底,眼细辨,双手就能摸索到,抠出,抱上来。这需憋气久,肺活量大,水性好。
用尼龙丝网兜,装一大兜,出水重四五十斤沉。背着游过四道江。看的游泳钓鱼洗衣的人一愣一愣的。实际蛤蚧在水中漂浮无重量。泳人只起牵引作用。
抓蝈蝈。无翅的黑褐色铁蝈蝈,紫红色火蝈蝈,翠绿色豆蝈蝈,有长翅的蛤蟆蝈蝈,都是蹲在青草尖儿颤翼嘶鸣。蛤蟆蝈蝈受惊,飞逃。铁火豆蝈蝈蹦逃。跳下草根,衰叶烂草,色彩驳杂,与之混为一体,根本无从分辨。
看盲流挖沙人。这是最苦最累的活儿。按米计价。每天甩开膀子能装二十马车江沙。赚九元钱。干这活的老客,多系劳教释放人员等徘徊社会边缘的各色人。
冬天室外零下三四十度。住在四壁尺厚冰霜的沙地窨子里,零下三二十度。只没风而已。现搂草煳包米馇子,烤土豆当饭。有时地窨子塌了,就闷死在里头。
夏天蚊虫叮咬。早先还有饿狼窥伺。
四道江对岸是莽格吐,卧牛吐。古辽金人聚居区。龙兴之所。金兀术坟墓在那儿。稀奇古怪的地名多呢。“齐齐哈尔村”,“富拉尔基”区,“梅里斯”区。
“歌舞团”四合院最大的官姓张。华国锋主政时到黑龙江视察,问省委杨易辰书记,你北平中国大学法律系同学任仲夷主政辽宁。还有个姓张的同学呢?杨答没任要职。
张的入党介绍人是陈毅。
张五七年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从最高法下放东北。
始任大庆书记,未到任,再改派大学书记。
张十一级。文革后升至九级。
张是个和善仁慈的老者。胖胖乎乎。脸面保养的像刚出锅的白面馒头。我曾在一米多的距离见过李德生。那保养极佳的面孔,跟张很相似。
一般一个门洞住三户都挺宽敞。张一家住一个门洞。好多房间空着。他小儿子常领我到他家打乒乓球。他小儿子现居北京。他大儿子是领我游过嫩江的第一人。现退休居齐市。数学教师。
我是六八年底离开那里的。走时,那已被文革闹腾的面目全非。人际关系和文化底蕴已遭数度浩劫,万户萧疏,彼此陌路。
赞赏
人赞赏
北京去哪个医院看白癜风比较好北京白癜风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