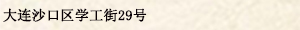老家房前屋后消失的小河
老家,我已经离开多年,确切地说,我是在年夏天离开的,那年我七岁,当时是为了回到城里上学,可是我很不情愿,死活都愿意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可父母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我应该回到城市里读书,城里的教育资源更好,况且城里的家附近的小学是区重点学校,师资力量以及配套设施都比较好,就硬拉着我回到了陌生的城市。
我走之前,我还跟村里的玩伴都告了别,至于剩下谁没通知到,我也都忘记了,我想等我走后,她们都会马上知道,并且她们会很想我吧,因为我一直很想她们的。我清楚地记得,我走的时候,爷爷奶奶身体还算可以,除了年长一些外,在那整个村子里也属于年长的,其他的我还没感觉会很快相继离去的。我还记得,老家的房前屋后一共有三条小河儿。
西南边的小河儿相对比较来说算是最大,也离奶奶家最近,出了院子,往西一拐就是一片苞米地,苞米地的尽头就是,小河从这边望不到对岸,里面夏天有茂密的水草和小鱼儿,哥常在那里用捂子捂鱼,鲫鱼和泥鳅居多。大孩子们可以随意去那里游泳,我却不敢,哥看着我也不让我去,说是我自己一下去就会被淹死。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也就是让我在岸边坐着看着,只可以把双脚耷拉在水里一会儿就得,然后就撵我到岸上的碾盘上帮他看衣服。那碾盘直径能有3米,爷爷说那是早年生产队用来碾米用的,至于怎么碾米我从来没看见过,也好奇中间怎么那么大一个圆窟窿,有脚能伸进去那么大,我们一般在上面玩泥巴的时候还得避开那地方。四周没有树,种满了庄稼,庄稼品种种得很单一,不是高粱就是苞米,没有一样是我爱吃的,那时候还不舍得都掰青苞米吃了,而我就仅仅爱吃青苞米,所以我对周围大片庄稼的兴趣完全没有瓜地那么浓,想看瓜还得去村东边村里的瓜地。
河里那些水草水上部分也有一人多高,采摘上面的嫩穗可以吃,不是怎么好吃,吃不吃都行,估计乡下能吃不能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毒吧,河面上的两种水草也有可以吃的是它的根上有种子,这个确实可以吃,叶子像袖珍荷花一样水面上浮着,把它的梗抓出来,扭下根下面的种子然后再扔到河里就行,说是能继续生长。现在都好多年不见了,我确信我还能认识它们,是跟西南边的小河一起认识的,在以后的各地的小河里没有再见过。我一直记得它们的名字,但是至今也不知道那些字怎么写,或者学名叫什么,有机会真得仔细查查。很奇怪的是,西边这条小河的南边原来的低洼处居然不知道啥时候垫起了土堆,哥说那叫房身,然后就盖起了房子,一户人家就搬来住了进去,跟原来那村子两趟房不在一起,就那么孤零零地存在着。平时有大地里的庄稼挡着看不见,等一到做饭时候,那里也跟着冒起了炊烟,现在想想,原来村子里的两趟房旁边由于有河的缘故,没有多余的地方扩展了,那户人家是另起一行的,也算是外来户的坐地户吧,不跟大家一个姓,这个村子是个姓氏村。
我听哥的话也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不让下西边那条小河,我却常跟伙伴儿去后边的小河,并且有一次真差点儿淹死,那时候要是淹死也就死了,也就没有后来这么多废话了。后边的小河跟奶奶家隔一趟房,前后趟房中间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小道儿,可以赶马车过。穿过后趟房谁家或者是绕一圈,就可以到后面的小河儿边游泳去了,我总是主动去找那些有的叫姑有的叫姐妹的去玩。在她们的鼓动下,我也半会半不会地学起了游泳,就是把脑袋伸进水里的狗刨儿,另外两个可以互相摁着脑袋在水里玩,我不敢去按她们,因为我自己都是勉强保证不沉下去,但其中一个却过来把我按了下去,我咕嘟咕嘟地喝起了水,呛得够呛,要不是我拼命挣扎估计那个夏天的那天就没了。我在水里一直说着:烦人!烦人!她们居然还笑我,因为烦人这词的确是一句城里话,那是我回城上学的第一个暑假的时候。
后边小河给我的记忆,除了差一点淹死外,就是挨着后面小河的几户人家也比较陌生,陌生的大多数是外来户,但是尽管陌生,挨家挨户我也都去过,他们家都没有跟我能玩的伙伴,有的都是老年人,也就是我得管叫爷爷奶奶的,有的是我管叫哥哥嫂子的,他们的孩子都很小。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当时怎么想,居然每家都去串过门,有的还吃了人家烀苞米、烧土豆啥的,尽管奶奶多次告诫我,人家吃饭时间不能去串门,谁家给啥也不能吃,别让人家笑话,尤其是个丫头,更不能馋嘴。我还真没管那个,到了谁家没个准点儿,半拉苞米面饼子吃得也挺香,有的人家还放了糖精的,更好吃了。他们那些人家对我也都很友好,知道我父母在城里,也知道我是谁家孙女、谁家女儿。还有的我最不爱听的话也时常从他们嘴里冒出来,说我如何小时候里吃过谁谁的奶之类的,的确是有那么回事儿。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把我从城里扔给乡下的爷爷奶奶抚养,奶奶开始就是抱着我挨家挨户找人给我喂奶,我也就吃遍了那里的同龄人妈妈的奶了,奶奶的意思就是吃一口得一口,促使奶奶常常抱我去讨奶的原因就是,那时候我长得大脑袋小细脖地,怕不好养活。可是谁要是说我大眼睛双眼皮儿挺好看,奶奶就很高兴,谁要是事实求是地说我有点对眼儿、还奔儿楼瓦块地,奶奶就不愿意。我的头发还稀拨愣登地黄,想扎个小辫子都勉强。怪不得那个小伙伴敢把我按水里,估计是不怎么待见我,并且我又生性软弱。
其实跟我在后边小河里游泳玩的根本不是我最喜欢的伙伴,我最喜欢的伙伴还是东街的几个,就是家住在靠东南边小河边的,我都得叫这姑那姑几姑的几个人,她们一家一般都有几个孩子,大孩子们通常也是跟我几个堂兄弟姐妹一起玩的,小的几个跟我玩儿。我跟着她们到处跑,东边除了有村委会,还有小砖窑,再有就是一片日夜有人看着的西瓜地和香瓜地,整天看得很紧,跑不快的根本不敢去那里踅摸着啥,周围也不封闭,就那么让人眼馋不敢动。我能借光的时候,就是大孩子们偷完没熟扔下不要的小瓜蛋儿,有的甚至是被咬了一口有些苦的,我也要来翻个面再啃两口尝尝也咽了下去。除了玩以外的大部分事情都与我无关,每次我出现在大人们面前,他们都会提起一下我的父亲,父亲每次回乡下也都各家拜访拜访加深印象,而且还不忘嘱咐他们,说我在那里希望多多关照,意思就是别让他们家孩子欺负我。即使被人欺负了我也不好意思说,好像很没面子一样,一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奶奶呢,是个小脚,走哪里都不方便,我也挺不理解别人怎么不能帮助一下奶奶呢?比如别人家树上的桃子、李子、杏子成熟了就不能多给咱几个?开始也挺纳闷,家里的园子怎么就不种几棵果树呢?那样的情景多好啊!后来听大伯说,家里人口多,全靠园子里的地方种些蔬菜维持生活,要是园子里有果树的话,就欺得庄稼不爱长。我还是想,哪差那一块地方种那破白菜啊。那就顺其自然吧,也有一次用土块砸了一个远房堂弟,听着他疼得嗷嗷哭的声音我愉快地跑远了,头上两个旋儿的他的确欺负了我好几次,最可恨的一次是他把我推到东边的小河里的,我自己扑棱扑棱爬了上来,一身泥水哭着回的家。
从那以后,奶奶不让再去东边玩,怕再遇到他把我塞河里出不来。那个夏天我都乖乖地待在西边,出门远远看见他也很快躲回屋,仿佛整个村子东边都被他霸占一样。直到冬天来临,河水都冻住了,我才有机会再去东边看河。去的时候冰面正被村里人刨开一个大洞打鱼,还不让小孩靠近,怕滑到冰窟窿里去。我就远远在站着,看着本来活蹦乱跳的大鱼小鱼一条不剩地被他们捡走,然后被上称挨家挨户按照人口分下去,自然分啥也没有我的份儿,分猪肉也没有我的份儿,我户口不在那里,也有人看见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口头安慰了我。
随后不久我在当地上了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跟着姐姐们去,学的也不咋地,所以才回到城市来上学,可是还是很想那里,想爷爷奶奶,想大伯一家的兄弟姐妹,也想西院的堂叔家的兄弟姐妹,甚至也想那个远房的堂弟。原来班里的同学也是记得比较清晰,而且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一部分同学的名字,就是不知道他们记不记得我了。回来正式上学以后,学校里的教学资源真的如父亲所说挺好的,可以参加各类学习比赛,我雨天鞋子、裤子都湿透了也在答卷,得到的奖品除了奖状就是本子和笔,也就几毛钱的东西居然很高兴。每次放寒暑假也许会有机会回老家看,爷爷奶奶都老了很多,由于思念我的缘故,都病了几次。西南边、东南边、后边的小河也都陆续被填平,盖上了房子,现在的三排房子的村子人口也增加一些,搬来了一些外来户,我也再没有机会去认识他们了。再后来,爷爷奶奶、大伯等长辈们又相继离世,我都没能有时间一一去送别终成遗憾。
近些年时间充裕了写就时常再回去,大部分去也是因为平辈的兄弟姐妹们家中的大事小情了,他们首先就会想到我,而我也是趁此机会再看看家乡周围的一切。变了,变了很多,茅草房也没有了,都是镶嵌着琉璃瓦的砖瓦房了。马车偶尔有,家家都有农机具,农用车、自用车也很常见,院子里屋檐下也都是水泥铺就,都留着对开的两片园子,院子里都至少种着棵果树,春天满院子的花,秋天满院子的果实,这样子才是我很小那时候希望看到的景象。而乡亲们的家里又都剩下了老年人看家种地,年轻一点的也都进了城市,偌大的三间瓦房都显得宽敞明亮,一个大炕睡几口人的情景是历史了。还发现不单是那三条小河再也没有了,那个大碾盘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北京哪家白癜风医院治疗好北京看白癜风那个医院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