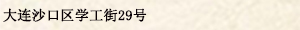木兰影视路遥纪录片第七集大寒
读经典美文,做智慧女人——欢迎走进木兰书院,邂逅生命中最美的传奇!(点击标题上方蓝色小字“木兰书院”,免费订阅《木兰》微刊,与众多花木兰成为同伴!)
谨以此片纪念当代作家路遥先生
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第七集大寒
(路遥)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铺过。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
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那时候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四十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经过一阵敲敲打打的巫术之后,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第二次,我上山砍柴,在当时的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
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转过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
是的,这是命运。但是,我对命运的无情,只有悲伤和感叹。痛苦,不仅是肉体上的,主要是精神上的。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感觉,我说过,我绝非圣人。这种宿命的感觉也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有一定“依据”的。我曾悲哀地想过,在中国,企图完全长卷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死不瞑目。伟大的曹雪芹不用说,我的前辈和导师柳青,也是如此。
老实说,我之所以如此急切而紧迫地投身于这个工作,心里正是担心某种突如其来的变易,常常有一种不可预测的惊恐,生怕重蹈先辈们的覆辙。心越急,病越重。出于使命感,也出于本能,在内心升腾起一种与之抗争的渴望。我想起故乡榆林地区的中医有名。到那里病治好了,万幸;治不好,也可就地埋在故乡的黄土里,这也是最好的归宿。在这个创造了你生命的地方,会包容你的一切不幸与苦难。就是生命消失,能和故乡的土地融为一体,也是我最后一个夙愿。
带着绝望的心情离开西安,向故乡沙漠里的榆林城走去。故乡,又回到了你的怀抱!每次走近你,就是走近母亲。你的一切都让人感到亲切和踏实,内心不由泛起一缕希望的光芒。踏上故乡的土地,就不会感到走投无路。
(原陕西省纪检委书记李焕政)有一次去看路遥,路遥说:“哎呀,精神很不好。”在西安检查,说他的肝上有毛病。我说:“那好办嘛!王震的病,西安、延安看不好,就是咱榆林的中医给看好的。”路遥就说:“啊呀!那好么!那就同意你的意见,叫你这个老医生给看看。”所以,就把这个老医生张鹏举请来,给路遥开了些中药。
(路遥)张老开始调整我的整个身体,我像牲口吃草料一般吞咽了他的一百多副汤药和一百多副丸药,身体开始渐渐有所复元。身体稍有复元的时候,我的心潮又开始澎湃起来。问题极自然地出现在面前:是继续休息还是接着再写?按我当时的情况,起码还应该休息一年。所有的人都劝我养好身体再说,但是我难以接受这么漫长的平静生活。我的整个用血汗构造的建筑,在等待最后的“封顶”。
是否应该听从劝阻,休息一年再说?不行!这种情绪上的大割裂对长卷作品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么,还是应该接着拼命?自我分裂!两个分裂的自我渐渐趋向于统一,开始重新面对惟一的问题了,那就是必须接着干。蓬勃的雄心再一次鼓动起来。只要上苍赐福于我,让我能最后冲过终点,那么永远倒下不再起来,也可以安然闭目了。这将是一次带着脚镣的奔跑。
(原陕西省政法委书记霍世仁)年秋天,路遥同志来榆林,要完成他《平凡的世界》的第三部。有一次,我是早上八点钟开会,七点半就到他房间,到他房间里以后呢,看见他还在写呀,我说:“路遥,你晚上没有休息?”他说:“没有休息。”他上劲了,一定要一气呵成。
(路遥)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
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了某种“惊艳”,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入似乎也很顺利。
(王天乐)他就紧紧地抱着我,说他有一种预感,就第三部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中国在变化了,中国在有一种大的变化了,户籍制尽管消灭它是漫长的,但是它终于再没有什么意义了,说这个我已经感觉到来了。然后他就拍了我一下,说:“朋友啊,我们这一代可能见不到,我们一个发达富强的民族,但是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朝气蓬勃地努力,为此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农民的儿子,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就他说这话的时候,好像和我就不是弟兄了,是一种非常陌生的一种感觉。
(路遥)年元旦,如期地来临了,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地内疚。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
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揩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胜败毕此一役”之感。万分庆幸的是,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
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春天已经渐渐地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责任编辑叶咏梅)因为我们播了前两部以后呀,演员和我都期待着马上录制第三部。我说我已经开播不能停播,你第三部无论如何得六月一号交到我手里。
(路遥)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地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待不下去。
(王天乐)什么时候,说后天要走了,要离开西安了,路遥就会哼着民歌,在院子里告诉所有的人,甚至门房上的老谢,说我后天就回陕北了,多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路遥)这是一次漫长的人生孤旅。因此,曾丧失和牺牲了多少应该拥有的生活,最宝贵的青春已经一去不返。生活就是如此,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无论如何,能走到这一天,就是幸福。
再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从早到晚,从春到冬,从生到死。第一次将种子播入土地,一直到把每一颗粮食收回,都是一丝不苟,无怨无悔,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直至完成。用充实的劳动完成自己的生命过程。
我在稿纸上的劳动,和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本质上是一致的。由此,这劳动就是平凡的劳动,而不应该有什么了不起的感觉。由此,你写《平凡的世界》,你也就是这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员,而不是高人一等。由此,年5月25日,就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而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由此,像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开始你今天的工作吧!
时间在飞速地滑过,纸上的字却越写越慢,越写越吃力,终于为全书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几乎不是思想的支配,而是不知出于一种什么原因,我从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来到卫生间,用热水洗了洗脸。几年来,我第一次认真地在镜子里看了看自己,我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苍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我看见自己,泪流满面,索性用脚把卫生间的门踢住,出声地哭起来,我向另一个我表达无限的伤心、委屈和儿童一样的软弱。而那个父亲一样的我,制止了哭泣的我,并引导我走出卫生间。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沉默了片刻。在这一刻里,我什么都没有想,只记起了杰出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几句话:“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王天乐)我预感已经完了,门打开的时候,他就说:“记住,也许这句话对你是重复的,”他对我讲:“记住,也许这句话对你是重复的。但是我还要提示你,一个人一生中要完成一件重大的事件,必须以宗教般的信念和初恋般的热情才能做完它。你休想用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完成一项宏大的工程。”这句话,我经常勉励自己。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联播责任编辑叶咏梅)准点赶到,6月1号(年)赶到我们这,其实他那时候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王天乐)《平凡的世界》写完以后,千头万绪的事情这才开始要他处理,但是他的这种智慧和能力,就是处理日常事务的能力已经下降了。瞬间的这个激动——某一天我正在延安的一个县上采访,电话打通以后,他说:“我是路遥。”这个电话一打,我想这是一个天大的事,因为他一分钟就没说话,然后他说:“茅盾文学奖揭晓了,我获奖了,我是第一名。”我相信他哭了。这倒不是他看中这个奖有多大,这是一种认可,六年来的交织,六年来的这种悲苦,一生对文学的这种执着的追求,终于在某一个符号上承认了他。然后我就愣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会祝贺他的,但不是现在。我说:“有困难吗?”我相信一般人,在此时不会想到路遥有什么困难,但我就预感到他肯定有困难,他说:“有,我一共有五千块钱,我这回到北京不得够,我要买一百套书,送评论界、送朋友,我自己要存一点书,我最起码要请一桌饭,我所有的开支不到三分之一。”
当时的钱那是多么贵重,几千块钱就可以拯救一个家庭,这样的问题对我来说,你不能说没有,你和他不能讨论说“那怎么办?”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写了一部书,获了这么一个大奖,没有钱去领奖,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说,写作为了什么,我们就那么崇高吗?我们崇高得连我们生存都没法生存了?而我要给他借一笔钱,搞一笔钱,可想而知,它就是犯罪。但是作为你自己来说,你就会理智地考虑,文学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付出?为什么苦难怎么就降在我们家的头上?文学固然美好,它曾经伴随我度过了那么多幸福的时光,但是一旦降临在你的头顶上的时候,你又觉得它这么肮脏。就我觉得,这门学问,我永远再不会提及它了,就当时的感觉,我再也不会读任何小说,我就觉得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我从事的职业才是真的,尽管人家让我假写,我都会写成真的。
这是这种狡辩,这种批判,完结了以后你还得活下去,你还得要完成这个事。我后来就找到这个(延安)地委副书记(冯文德),我就把路遥的这个情况一说,这个人是人大毕业的,俄语特别好,他就用俄语说:“如此荒唐!”然后他就走出这个桌子,握住我的手,“我们现在出发,一切由我来解决。”这人现在已经走了,但是他整个对我的帮助,这样的人的帮助,就太多太多了……回去以后,他把这个信封就给我,“你问他(路遥)好。”
这样,我就飞奔一样地(赶到西安),这是多么的残酷,我突然想起在《人生》获奖的时候,我就在这个地方给他送的钱,那时候我还是煤矿工人,整个领奖拿块钱,当时钱很贵,我就要给他送五百块钱。今天我又是这样来借的钱,他站在火车站,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发车了,他提前到的,他说:“顺利吗?”我说:“还很顺利。”我说:“以后啊,你就不要获诺贝尔文学奖了,去那儿的时候是要外汇的。”我说:“人民币怎么都好搞,恐怕外汇你我都搞不到。”他看了我半天,就上火车了,他不愿意再和我对话了,说:“日他妈的文学!”包子一甩,就上了火车。
下集预告
无论我们在生活中有多少困难、痛苦甚至不幸,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为我们所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而感到自豪。
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的劳动,像土地一样的奉献。
影像及图文综合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木兰书院
木兰微刊投稿邮箱:mlsy38
sina.白颠凤怎么治白癜风病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