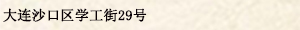黑龙江国海母亲的老屋
作家在线·散文
国海,年生于林甸县三合乡东升村,年毕业于泰来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分配在林甸县糖厂机关工作。工作两年以后便辞去工作只身投入商海,起起浮浮二十余载,虽无建树,但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文学的梦想,喜欢诗一样的生活,自由随心且无拘无束!
母亲的老屋
国 海
岁月如歌,那在指尖轮回的亲情始终在岁月里徘徊着,让我时常想起乡下的母亲以及母亲的老屋……
——题记
一
母亲是随着外公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从老家山东禹城挑着一副行李卷,逃荒到东北我父亲居住的那个屯子,那是位于双阳河畔下游南岸的一个小村庄,那时母亲才仅仅16岁,当时正是我们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一个时期,由于山东自古就人多地少,加上自然灾害,很多家庭因为没有粮食吃被迫逃荒和流亡,父亲居住的那个屯子当时是三合公社东升大队三屯,叫赵家围子。
一无所有举目无亲的一家人,被善良的村民收留了下来,因为没有地方安身,就让我的母亲一家暂时先栖住在生产队的大队房子里,那时的乡镇还都不叫乡镇,叫人民公社,村屯也不叫村屯,叫生产队,乡里乡亲的都叫社员,生产方式还停留在大锅饭大帮轰的集体经济时代,说是生产队的队房子,其实就是那种连脊的大土坯房子,紧邻着牲口棚,里面圈养着生产队的命根子——牛马等牲畜,也是生产队里的社员早上出工,晚上收工集合,平时开会记工分,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的地方,队房子里面有一个大通铺,能住着好几十号人,外公领着一家人就暂时住在那铺大通炕上,靠着乡亲们的救济,渡过了到东北以后最艰难的一段日子。
当时爷爷是生产队里的更夫,是最早结识外公一家人的东北乡亲,爷爷家当时的成分是富农,家有三个儿子,在阶级斗争及唯成分论的那个年代,成分好的人家都不愿把姑娘嫁到这样的家庭,怕受牵连,所以父亲连同两个叔叔一个成家的都没有,不过爷爷家在生产队里的人缘却很好,贫苦的社员们骨子里还都是很善良很淳朴的,爷爷见外公一家人挺可怜的,初到东北,无依无靠的,就说服奶奶把外公一家人安置到了自家三间泥草房的西下屋,也算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收留了我外公一家人,出于感激也好,还是好人有好报也罢,在队里一些好心人的撮合下,母亲就来到了爷爷家,嫁给了父亲,那个年代别说媒妁之言了,只要能有一口饭吃或者有一个安身之所就可以领回来一个媳妇,只是不知道当年的父亲母亲之间是否有过感情,抑或是爱情...
二
转眼的十几年间,我们兄妹五人便相继来到了这个世上。
记忆中的童年就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没吃过一顿饱饭,总是在一种有上顿没下顿的饥饿和寒冷中渡过的,从物质到精神都是贫穷的一清二白。苦日子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才慢慢地好了起来,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改革的春风给广大的农村和农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和生机,先前的生产队解体了,人民公社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大帮轰大锅饭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乡镇村屯又恢复了以往的的称呼。
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变了,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分产到户,每家每户除了分到了相应的土地,还分到了相应的农机具和牲畜,我家当时就分到了一套农机具,一架马车,还有一匹青灰色带白花的沙栗马,还有部分生产工具,这给原来就特别能吃苦肯出力的父亲也带来了新的干劲和盼头,带领两个尚未成年的哥哥种地之余,还搞起了副业,除了到北河套打渔之外,夏天打羊草,冬天下苇塘,冬闲的时候就编苇席和草帘。全家人把投出来的优质的苇子扒掉皮做成工艺苇帘卖到城里,用烧不尽的苞米叶子编牲畜用的套包,用秋天割来的柳条编筐土篮子还有簸箕粮囤子。而最忙碌的还是母亲,做饭养猪,喂鸡喂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起早贪黑的为一家人提供着后勤保障,虽然很苦很累很辛劳,但是一家人却再也不挨饿了,那时的农民能有什么资源和资本呢,最不缺的就是一身的力气和吃苦耐劳的干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爸爸带领我们家人硬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在我们村里盖起了第一撮砖挂面的三间宽敞的泥草房,那是爸爸的骄傲,也是我们老“国”家的骄傲,脱坯、买砖、房木、门窗,省吃俭用,当三间崭新的房子矗立在我们老“国”家的当院,父亲母亲还有我们一家人都开心的笑了,其间吃过的辛苦和劳累只有我们一家人心里知道,那是爸爸用多少汗水和辛劳才换来的。可人的命运谁也说不清,就在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好的时候,也许是常年的起早贪黑的劳累奔波,也许是没日没夜的辛苦劳作,要强的爸爸从没有爱惜过自己的身体,在盖完新房子的转年,身体透支得特别厉害,原本身体硬朗的父亲却突然感到浑身无力,胸闷喘不上来气,还咯血,一向刚强的父亲,直到拿不起生产工具到地里干农活侍弄庄稼时,才被妈医院去看病,结果检查一出来,是风湿性心脏病晚期,在那个年代无可医治,听了这个消息以后,我们一家人就彻底的崩溃了,天似乎一下子就塌了下来,而此时的母亲却异常的冷静,她明白,爸爸倒下了,她不能再倒下来,于是把家里当时所有值钱的东西,能吃的能用的,包括鸡鸭大鹅,以及没有出栏的两头肥猪和一头母猪都卖了,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把家交给了两个大一点的哥哥,就医院里住了下来,可最终爸爸也没有再站起来,也许是爸爸真的累了,要到另外的一个世界去好好的歇歇吧!从发现有病到离开我们仅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那年我刚刚只有13岁,从父亲有病住院到临终前,我都没有再看到一眼父亲。据日后母亲回忆说,即使在父亲病重住院的最后日子里也特别的刚强,没有一丝的害怕和恐惧,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母亲和我们兄妹五人,父亲出殡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瓢泼的大雨整整下了一天一夜。
送走了父亲以后,母亲在父亲留给她的唯一的老屋里,没有掉一滴眼泪,怀里抱着爸爸的照片,在父亲生前睡过的地方静静地坐了三天三夜,水米未进,我们都吓坏了,止不住的都哭了起来,这一哭才把母亲从痛苦和绝望中唤醒了,看了看我们五个嗷嗷待哺的儿女,慢慢地放下爸爸的照片,把我们五个兄妹紧紧地抱在一起... 一瞬间我们都成了无依无靠的苦命的孩子,为了给父亲治病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积蓄,还借了很多外债,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就全落到了只有37岁的母亲一个人身上,所幸的是母亲把所有的苦难与艰辛都扛了起来,用她山东人骨子里固有的勤劳顽强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默默地担起了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凭一个人的力量,把我们尚未成家的五个兄妹一个个拉扯大,并最终都成家立业,那时的母亲就像是一头永不疲倦的老黄牛一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和劳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母亲从来没有向村里乡里要过一分钱的补贴和困难补助,党和政府也从没给我们这样的家庭一分钱的救助,所有的贫穷和劳累都是母亲独自一人承受,也许是忠贞的坚守,也许是承诺的坚守,承受着苦难,却放飞着儿女,母亲把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以及心血都给了我们儿女,把最美好的生命年轮刻在了我们儿女成长的路上,也把最最美好的时光岁月都洒在了家乡那日夜流淌不息的双阳河水中。
三
那个年代对于孩子的上学读书的问题都是很随性的,在农村的潜意识里认为读书无用的还是占大多数,尤其是刚刚经历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对于读书的理解还很谬误,尤其是孩子多的人家,爱念就念,不爱念就下地干活。不过在我的记忆里却是因为两个哥哥的上学问题,没少挨妈妈的打,不知打飞了多少笤帚疙瘩,打归打骂归骂,背地里心疼地却偷偷地流泪,因为母亲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在母亲的心目中她可以容忍贫困,但她却绝不容忍我们无知和愚昧,两位哥哥就在妈妈的打骂声中都读到了初中毕业,父亲去世以后,带着父亲生前的嘱托,为了把爸爸留下的家继续支撑下去,母亲毅然的做出了一个痛苦而又艰难的决定,读到初中毕业的两个哥哥下来种地,我们三个年幼的弟弟妹妹继续上学。
两个哥哥就在妈妈的眼泪和无助中离开校门,和母亲一道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扶犁铲趟,种地打草,挖菜养猪,继续着父亲生前所有的劳作,不同的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由父亲变成了母亲,岁月的艰辛把母亲一步步的打磨成农家的行家里手,无论是春种秋收,扒炕抹墙,还是脱坯打场,烧碱熬糖,样样在行,无论是侍弄庄稼还是操持家务都弄得井井有条,虽说还是清茶淡饭,粗衣布褂,但却很干净整洁,温馨舒适,有了两个哥哥的劳动和帮助,母亲带领我们一家人在最艰苦的日子里,硬是把要塌下来的天又给撑了起来,也撑起了我们一家人对未来的希望!看见两个哥哥都下地干活了,我也想不上学了,下来帮母亲干活,为了这件事母亲拿着笤帚疙瘩不知打了我多少回,每次都是一边拿着笤帚打我一边流着眼泪,硬逼着把我撵回学校上学去。记得当时还特别的恨母亲,现在再回想起这些,从内心里我是多么地感激母亲,因为有时候人的命运的的确确靠知识是可以改变的,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母亲都没有让我们放弃对知识对读书的渴望。一边打我一边骂我:“你两哥哥已经不上学了,你再不上学让我怎么对得起你爸爸,你给我记好了,从今往后家里的事情不用你惦记,你就给我好好的念书,不但要念书而且一定还要念好,你爸爸不在了,就要给妈妈争脸,给咱家争气,我不能让乡亲们看咱家的笑话。”骂完又是一顿狂风暴雨,打完以后就坐在地上抱着我呜呜的哭...为了不再挨打,也为了母亲的眼泪,从此以后我就一门心思的发奋读书,刻苦学习,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那个年代唯一的一所中专院校——师范学校,也是那些年我们屯子里第一个通过读书而走出庄稼院的年轻人,不但给妈妈长了脸,也圆了妈妈的一个心愿。当时是靠母亲辛辛苦苦养了四年猪,才供完了我的全部学业,每一个要开学的日子,都是母亲最难过,我最痛苦的时候,不管是多么的难多么的苦,母亲总是能把我一学期的学习费用准备出来,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觉得我手里捧得就是一座山...每一个上学离家的日子,都是母亲一个人把我送到村口,在村头的那棵老树下,风吹散了母亲凌乱的头发,也曾有过黑亮的眼睛黑亮头发的母亲,却在不知不觉中苍老了许多,母亲的眼里总是充满了希望与怜爱的泪光,一直到我消失在她的视线中,那个身影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忘记……
这也时常让我想起当年送孩子去外地读书的情形,望着孩子渐渐远去的背影,那一瞬间心里也常常是酸酸的,可想而知,当年母亲的那种心情比我沉重不知多少倍。在外读书的四年间,母亲挨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只有我心里知道,其间母亲不但还清了家里所有的外债,还在老屋里给两个哥哥都娶上了媳妇,而且还迎来了我们“国家”第三代人的降生,我们“国家”终于在母亲辛勤汗水的浇灌下添丁进口了,母亲常年紧锁的眉头也终于舒展开了,脸上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记忆中的母亲从来都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没有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手上永远都是剥了一层又一层的老茧,在年因胆结石手术住院期间,在医院里平生第一次为母亲剪了指甲,当多少年以后,我再次抚摸到母亲的一双苍老而又粗糙的手时,那一瞬间我的眼里全是泪水...
四
生活中有两件事是让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就是母亲的孝顺和善良,在我们家乡的那个小屯子里也是有口皆碑的,奶奶去世的早,爷爷和最小的叔叔一起生活,家里还有一个瞎爷爷留下的的傻大爷也在叔叔家,叔叔家里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日子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无论是平常日子还是年节,只要是家里做一些好吃的东西,妈妈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爷爷送去一份,一年四季从未间断,遇到年节的或者家里有个大事小情的就把爷爷接家里来,好吃好喝的伺候着,让爷爷享受着我们这个家族至高无上的待遇。
爷爷和傻大爷平日里穿的戴的铺的盖的都是妈妈给做的,还有一些拆拆洗洗缝缝补补也都是亲力亲为,从来没有嫌脏嫌累过!直到爷爷和傻大爷去世,有时我就想,母亲那时真是替我们儿女做了很多应该我们做的事情,尽了我们该尽的孝心。母亲除了对老人和子女家人的付出以外,和左邻右舍的乡里乡亲们也都是相处的特别好,母亲热情开朗豪爽大气,屯子里无论是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或者是有求助于母亲的,母亲都是不遗余力的给予帮助,每年都把自己园子里种的吃不下的青菜,大筐小篓的送给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把自己家孩子们穿剩下的旧衣服旧鞋袜送给屯子里更困难的乡亲。遇上红白喜事的时候,谁家亲戚多住不开的时候,都愿意到我们家来找宿,一是宽敞,二是干净,三是母亲的人缘好,可以说在母亲的身上你能找到所有劳动人民的淳朴善良和美德。早些年一些到屯子里讨饭的孤寡老人和妇女孩子,母亲除了给米给面,还给他们一些穿剩下来了的衣服,赶上饭口了还留家里吃一口饭,就连那些耍把式的卖艺的唱戏的,只要不嫌弃,母亲都要领家里来给他们做一顿热乎饭,有时还把西下屋收拾出来给他们住宿,炕烧得热乎的,给她们盖最好的被褥,感动的她们离开我家的时候跪在地上直给我母亲磕头。
因为母亲小时候就是逃荒到东北的,她知道要饭流浪的滋味,她知道人离家在外的不容易,所以总是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在母亲的人生字典里一是吃苦耐劳,二是乐善好施,三是自强自立。所以母亲在我们的家族乃至整个老屯子里都是最受尊重最受爱戴的人。那些年屯子里这家丢鸡那家丢鸭的,而母亲家却连一根柴火棍都没有丢过。
另一件事情就是母亲为我们儿女做羊毛被的事情让我终生难忘,每年夏天,母亲用自己卖鸡鸭鹅蛋和青菜蔬菜的钱,换一些养羊户家的羊毛,给我们儿女做羊毛被,刚剪下的羊毛是很脏的,羊毛上面不但粘有泥土和碎草末子,而且还有一股熏人的膻腥味,特别是那些整张的羊毛,卷在一起擀毡了一样,特别的不好清洗,而且除膻去腥也是一个难题,可母亲自有她的土办法,坐在院子里的土井旁边,用洗衣粉洗去羊毛里的的泥土,洗过三四遍后再用棒槌敲打若干遍,再把羊毛浸泡在院子的一口大缸里,然后母亲就到村外的大坑里去挑一些黄土,等羊毛泡了七天以后,再把黄土和成稀泥,跟羊毛和在一起,用棒槌反复敲打,让黄泥彻底沁到羊毛里,然后就把粘有满身黄泥的羊毛放在事先备好的浴盆里,继续发酵,三天以后把羊毛从浴盆里拿出来,用井水把羊毛上的黄泥全部洗掉,羊毛的腥膻味就彻底消失了,经过妈妈这样处理以后,羊毛一点膻味也没有了,羊毛也变得雪白绵软了。妈妈就用这种羊毛加上棉花,为我们儿女做羊毛被子,那羊毛被子真是又薄又轻又暖和。母亲把一针针一线线,还有一生的幸福温暖和母爱的情怀,都缝进了我们儿女成长的悠悠岁月里。因为母亲有了这个手艺,邻居家的孩子结婚做新被子都找母亲来帮忙。我们心疼她累,劝她不要再做了。而母亲每次听了都是笑呵呵地对我们说:“趁着我现在还能动弹,就多给你们做点,早些年,家里穷,咱们做不起,现在你们都大了,日子也好过了,虽然都不缺啥少啥了,可妈妈就寻思着给你们再留下点啥,将来也是一个念想不是”。
听母亲这么一说,就浑身一颤,心里一紧,鼻子一酸,眼睛刷的一下就模糊了。现在我们兄妹五人的每个家里,都有母亲给我们做的羊毛被,盖在身上很轻很暖和,还有一股淡淡的清香,我知道,那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五
每年的正月初八都是我们家族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也是母亲最开心最快乐的一天,这一天是她老人家的生日。
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我们兄弟姐妹和母亲大团聚的日子,每年的初八早上,母亲总是早早地起来,把老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自己也穿戴得整洁利索,站在院子里迎接着她远方的儿孙们。每年的这一天,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无论多忙,都要回到老屋看望母亲,本来春节就是团圆的日子,又赶上母亲的生日,哥兄妹们就是一个字,就是往家“奔”,一是团圆,二是祝寿!这一天,老屯里的一些亲戚朋友,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也都来给妈妈祝寿,加上我们“国家”的这些孙男弟女,每年都有四五桌的酒席,欢欢乐乐,其乐融融,母亲坐在热炕头上磕着瓜子喝着茶水在招呼客人。而她的四个儿媳妇,四个妯娌,一个姑娘亲自下厨,洗菜择菜,切菜炒菜,炖炒煎炸,热气腾腾的,有说有笑,忙得是不亦乐乎。我们兄弟几个就和屯子里的叔叔大爷们坐在炕头上唠着家长里短和年景收成,屯子里的老亲少友们,无不羡慕我母亲和这一大家人,因为每年的这一天他们都会看到我们给母亲带回来那么多的米面粮油,衣裤鞋袜,肉禽蛋蔬,瓜果梨桃,啤酒饮料这些生活用品,母亲家的小屋都快成小卖部了。
我们哥几个有的是打的回来的,有的是开着私家车回来的,那场面那气派自不用说了,试想想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乡村寡妇妈,能把儿女们养得这么有出息,能把家里过得这么红红火火,这么兴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天的热闹很快就结束了,晚上我们都聚到母亲的身边,一起听母亲给我们讲过去的那些往事,和我们小时候发生的一些难忘有趣的故事,有欢笑,有眼泪,但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感激母亲生养了我们,好多年了,一直都是这样的场景,有时我就想,如果能让时光的脚步永远停留在这一刻该有多好啊!让母亲永远都像今天这么幸福这么快乐!
六
母亲的年岁虽说越来越大了,可她依然居住在老屋里,保持着勤劳简朴的农民本色,过着她自以为安静平和的幸福生活,心里时刻都惦记着她远方的的儿女们,养点鸡鸭鹅狗,让这些个生灵陪伴在她身边,平日里就侍弄着老屋前的小菜园子。
说是小菜园子,其实是一个大园子,一个有着多米长40多条垄的大园子,将近一亩多,每年都是母亲一个人伺候,像伺候我们儿女一样精心,不用化肥,专用农家肥,除了种些日常农家小菜以外,剩下的空地就全种大苞米,然后在苞米地的空隙里再撒上一些个豆角仔。一方大园子,一片儿女情,每年夏天回去看她的时候,看见的都是母亲老屋门前的那一片绿油油的大园子,蓬蓬勃勃,绿意葱葱的,两米来高的大苞米就像一片大森林,人走进去就没影了,我知道母亲就在那片森林里,于是我就站在老屋的院子里,冲着那片大森林深情地喊一声:
“妈”——不大一会就会看见母亲从里面提着菜篮子满脸的喜悦地从森林里走出来,烀一锅大苞米,烀一锅土豆茄子,蒸一大碗鸡蛋酱,香菜臭菜小葱萝卜...记忆的老屋里一直都充满着浓浓的母爱,浓浓的亲情,浓浓的眷恋...平日里不忙的时候,就早早地起来侍弄一下屋前的小菜园子,吃完早饭,把屋里屋外的收拾的利利索索以后,然后拿起一把小茶壶,揣上点瓜子糖块,拎点水果,或者到小菜园里摘点新鲜的黄瓜柿子香瓜,到东西两院的老姐妹,毕大娘李大娘王婶家唠唠家常理短,说说闲话闲篇,以及岁月短长,喝着茶水,嗑着瓜子,打发着属于她自己的幸福自在的美好时光,一晃日头爷就落山了,母亲就不紧不慢的,拿起她的小茶壶,在故乡的小村子里,迎着夕阳和炊烟回到她的老屋里,简单的弄点可口的晚饭,再焼一把火炕,然后就是坐在热炕头上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想儿女了就跟儿女们通通电话唠唠嗑,每天都重复着这种平静舒心的日子。
我每次回乡下去看母亲的时候,总是劝她进城和我们一起生活,不让她再干这些又苦又累的农活时,母亲都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不知所措的笑笑,什么也不说,等我们真正吃到母亲亲手种的那些绿色可口没有污染的蔬菜时,吃到老屋的大铁锅炖出来的母亲饲养的大鹅小鸡时,才能真正理解母亲的心思,味道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可母亲却老的让我们心疼...每当我们要走的时候,母亲总把装满一腔母爱的大包小裹塞进我们的手里,黄瓜豆角茄子辣椒,角瓜倭瓜萝卜大苞米,大葱白菜土豆柿子,香菜韭菜芹菜以及自己腌制的鸭蛋鹅蛋,酱黄瓜荠菜疙瘩大萝卜等一些小咸菜,还有母亲特意为我们儿女做的最爱吃的辣椒末和农家大酱,冬天的时候,还把一串串的红辣椒,大蒜辫,菜丝菜干,粘豆包,冻饺子,以及新打下来的小米,刚磨出的玉米面,都要给我们带上一些,你不拿这些,她就要落泪的样子,让你不忍心拒绝,日渐苍老的母亲,每次见了我们回去看她,苍老的容颜似乎又焕发了别样的容光。如果住上几日,晚上母亲就把我们小时候睡惯了的火炕烧的滚烫滚烫的,灶膛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心也跟着在燃烧,每一次躺在温暖的土炕上,都像是一次温暖的旅行,让你的身心乃至灵魂都来一次洗礼,那记忆中的味道,还有记忆中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小火炕的温暖啊,我不知道这辈子到哪里还能寻找到?现如今,我们五个兄妹都早已成家立业,而且有四个从农村中走了出来,日子过得也越来越好,都有了各自的儿女,大哥二哥家的侄子侄女也都当了爸爸妈妈,我们家已是四世同堂了,母亲也光荣地晋升为太奶奶了,六个孙子女中,出了三位大学生,其中的一位考取的还是一所国家名牌大学,今年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我们“国家”真可谓是人丁兴旺,一代更比一代强。母亲该歇歇了,也该享享清福了,住在城里的我和弟弟妹妹就都想着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照顾她,让她好好地享受晚年,可母亲每次都是待不上三天就吵着回乡下,没办法,我们就只好怎么把她接来的,再怎么把她送回去,送回她一辈子都离不开的乡下的老屋。
母亲一回到乡下,浑身就像有使不完的力气,精神头似乎也年轻了许多。母亲经常对我们说:“你们呐,都不要惦记妈,只要你们都过得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妈这辈子风风雨雨的都经历了,苦日子也过去了,什么也不图了,心里就图一个儿女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等将来妈老了不能动弹的时候,再到你们身边,让你们尽孝。” 如今母亲已经70多岁了,依然生活在乡下的父亲生前留下的那间老屋里,守候着属于她的老屋,看着自己的儿女们一年一年的回归,盼着子孙们一轮一轮的团聚,母亲的老屋和坚守让我不敢回忆,太多的岁月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回忆太多的辛酸,让我不敢回想,没事的时候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力量让母亲三十多年来一直都坚守在那间老屋呢?是对父亲留给她的一种眷恋?还是对父亲的一种无限追思与怀念?抑或是对爱的一种坚守,一种对生命的承诺与托付所做出的牺牲?这也是母亲为什么在父亲去世这么多年一直都坚持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原因吧,所以我想说,母亲和父亲之间是有爱情的,而且是到死都不会分开的那种爱!只不过是换了生命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罢了。 母亲究竟在守候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在线责编 尚书)
推荐阅读
梁晓声|心灵花园王剑冰|通州,大运河之首张继炼|张继炼散文短章选粹许俊德|死亡的云锦张镭|读书刘力|说旅游彭吉明|遗落在湟水河畔的文明碎片司丽娜|那一日,转山转水转佛塔覃跃|狗日的面子(短篇小说)廖静仁|一方水土(组诗)秦汉|秦汉西部散文三篇秦锦丽|离别山地
内容转载自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最好白癜风用什么药最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