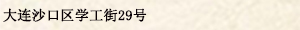王茂成秋天的那场意外
王茂成,年9月出生,江苏泗阳人,现居苏州,中国共产党党员,江苏省宿迁市作家协会会员。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雨花》《当代文学选萃》《当代原创文学》《短小说》、等刊物发表散文和小说多篇,其短篇小说《长寿面》获江苏省文化部、省作家协会“中国梦”征文优秀奖,短篇小说《秋天的那场意外》获第一届“红太阳”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三等奖。
秋天的那场意外
天气很热,河套里没有一丝风,一塘水似的西瓜地,叶子在暖烘烘的热气里打着盹。长长的柳叶坠在柳丝上无精打采,知了叫哑了嗓子,有一声无一声地低鸣。火球似的太阳落山了,大地笼罩了一层迷离灰暗的颜色。
这个时候,农家熄灭灶膛里的火,派小葫芦头孙子,或是刚过门的新媳妇,去河东买个西瓜回家,消消一家人一天憋在肚子里的暑气。
娃娃、小伙子、大姑娘、新媳妇一会儿就把秃子余老大的瓜摊围个水泄不通,称秤,收钱,找零,装袋,他一时忙的手忙脚乱。余老大忙归忙,嘴从来不闲着,有小伙子说,你看你忙成这样,瓜被人抱走两个,不付钱,你还不知道。余老大摆摆手说,这个你放心,拿走了一个,我们只当交朋友,去我瓜园的,我能让那一个空着肚子走?钱是小事,交朋友才是大事。
一提到交朋友,旁边瓜摊的许二鹅就咬紧牙关,把笑憋在一拱一拱的肚皮里,努力不让自己笑出声来。
余老大的瓜,很快卖完了,他拍拍屁股站起身来,把剩下的两个花皮香瓜切成几块,分给几个光头孩子说,都回家趴在妈妈的大奶子上睡觉吧,天亮了再来给你们讲古今(故事)。
余老大戴上破草帽,腋下夹着那杆秤向许二鹅笑笑,就走了。
余老大地里的瓜,不几天就卖光了,许二鹅地里的瓜,还剩下一大半,她心里很不是滋味,她恶狠狠地对坐在板凳上的丈夫章豆子说,快死起来,把瓜摊移到他那边,接接地气。
章豆子挠了一下耳边的短发,笑眯眯地说,相隔两步远,风水就不一样了?
许二鹅不理他,猛地把编织袋一抖,铺在余老大卖瓜的地方,她三下五除二,把瓜全部搬过来。嘴里没忘记告诫丈夫,没用的东西,今晚剩多剩少,你睡就在这里看着,不要怕半夜里鬼掐了你的头。
章豆子一听老婆要他夜里一人独自看瓜,心里有些惊悚的打冷颤,因为中午生意冷淡的时候,他又听了余老大讲起三十年前这里闹鬼的事,故事经过余老大的舌头一搅活,变的惊悚恐怖。章豆子天生是个小胆鬼,年近四十的人了,瓜棚里从来不敢住,瓜棚里过夜,多亏了家里的叔伯。
摊位搬过来真灵,朦胧的晚光里,人们分不清哪是余老大的摊位,哪是许二鹅的摊位,赶紧买上一两个西瓜,骑上自行车匆匆地往家赶。月亮挂在东天的时候,许二鹅的瓜摊子,还剩下几百斤大西瓜,许二鹅看着丈夫章豆子说,怎弄?今天买不掉了,你在这里看吧,我回家做晚饭了。章豆子坚决反对,不不不,我回去做饭,做好了,我叫叔叔来换你,你送我过前边的桑园地吧。
许二鹅生气说,看你那点出息,你自己过桑园子,鬼掐了你的头,我明天赔你。
章豆子惊悚地望望左右哀求老婆说,大天黑的,不要老说鬼、鬼的,胆子是天生的,我又不是故意的,余老大说了闹鬼的事,你剁了我的头,我也不敢一个人呆在这里啊。
无耐的许二鹅送走了丈夫,一个人蹲在月光下,她想把剩下的瓜拉回家,但这样做,很麻烦,明天还要往这里送,万一路上撞坏几个,就是几十块钱,这里夜里风凉,他叔叔来这里睡个觉,也省去了许多麻烦事。
月亮挂起来很亮堂,它在路边的渠水里像打秋千一样,一会儿把自己的脸压扁,一会儿又把自己的脸拉长,一只水刀郎过渠,把镜子一样的水面,弄出一线亮光。
有人拖着拖鞋,啪哒啪哒地向这里走来。月光下,余老大拖着自己长长的影子,一晃一晃地走过来。本村人是说笑惯了的,许二鹅远远就骂道,你秃和尚不在家睡觉,晚黑还到这里来,找魂啊?
余老大回嘴说,不是你在这里吗,特意来和你坐坐,想和你交情交情。
许二鹅笑说,弟媳妇不在,没人陪你坐,这交情也断了?
为了使读者明白前因后果,免得大家搞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赘述一下余老大的往事。
许二鹅的话,是有所点故的。余老大兄弟两人,都是光棍。二十年前的余老大是一表人才,小伙子长的在槐树庄是数一数二的。那年,他在运河南相好了对像,双方过了来往礼,女方把余老大留下吃晚饭。女方家做木工,专做棺木生意。前屋是木匠铺子,酒近半酣,突然女方家前屋电线走火,顷刻大火冲天,人们丧魂落魄救火。大舅娘子失声狂叫,我的巧儿还在床上啊!此时大火已经封门,余老大不管这些,蒙上一块湿布,硬是往里闯,结果,他把巧儿毫发无损地抱出来,自己却烧成了秃子。女方家找算命的一算,说余老大是火命,女方是水命,水火不相溶,相聚就成灾,婚事就此偃旗息鼓。前年,表兄从三河口带来一个女子,打算给他做媳妇。女子长的像土豆,但配他该是绰绰有余的。女子长的虽然矮小,但看起来精明、能干,吊梢眼里满是笑意,是个喜相女人。女子看了看前前后后的屋子,又去灶屋间端详了一番,对站在院子里的余二上下看了几眼,说,中。
晚饭之后,三十大几的余二不开窍,憨厚地坐在当间听大哥一个接一个讲笑话,月上中天的时候,实在忍耐不住的余老大叫老二去睡觉,余老大没有料到,这三河口的女子也跟着弟弟站起身来,她要跟着弟弟余二去睡觉。余二闷头闷脑地说,你是说给我哥的,我不要你跟我睡觉。
他转脸把门关死了。
女子坐在月亮下流眼泪,余老大在屋子里作了短时间的思想斗争,他来到院子里,对女子说,到屋里坐坐,不跟我,不要紧。
女子来到堂屋,委屈地说,看过门户了,我以为是他,才答应的。
余老大抽了一根烟又续了一根烟,眼里泛着泪光说,不要紧,今晚的新房我让给老二。
女子有些忍,知道余老大是个善良人,就嗫嘘着说,要······要不······我······我明晚跟老二!
余老大像没听见,把老二的房门打的咚咚响,他把睡梦中的老二拉起来,一把塞进自己的房间,说,这肥水还能流向外人田?
举行婚礼那天,余老大扳着手指头算人数。兄弟俩在窑上干活,那些兄弟姊妹们,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说话笑笑嗬嗬,你帮我,我帮你,老二办喜事了,他们总的都会来的。再算上亲朋好友,加起来要几十桌,这一头猪杀了怕是不够,那么就把两头全杀了吧。
可人心的尺寸,余老大没有把握准,他错把别人的一壶温水,当成自己的满肚热肠。窑上那些出苦力,拿血汗钱的兄弟姊妹们,是讲来往的,没有喜丧往来,人家是不拉新往来的。大热天,剩下一半酒菜没人上桌,晚上,他又请来全庄老少,才算消耗掉。
所以,余老大一提到交朋友,许二鹅就笑的肚子疼。
老二娶了媳妇,也生了儿子,年前,老二媳妇眨着一只吊梢眼,笑盈盈地和余老大商议,他大爷,我儿子和你儿子是不是一样?余老大神奇地望了一眼老二媳妇说,哪还有假,我又没有家眷,侄儿,侄儿,就是儿嘛!吊梢眼媳妇说,那好,你想不想你侄儿上个好学校,将来长大了风风光光?余老大一扭脖子说,你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谁不想自家的后代光宗耀祖?只要孩子有出息,我余老大剥皮卖肉都去干。老二媳妇笑笑,进一步说,他大爷,你是知道的,我和你家老二在县城开一家饭店不容易,眼看看你侄儿就要上一年级了,城里没房子,孩子也上不了好学校,这手里七凑八凑的,房钱还差一大节,我想把房子卖了,我们一起到城里去。余老大想想说,中,我去城里带侄儿,还能搞个铺子,替人理理发,家里地里收入不大,忙时回来收收种种就是了,你们先走一步。
余老大从家里搬了出来,他在桑园里造了一间小屋,准备秋种结束就去县城。
老二媳妇从县城回来了,手里提着大袋小袋的礼物,把余老大喜欣的不得了,他赶紧骑上自行车去集上买菜,一家人在老大的小屋里高高兴兴地吃着午饭。吊梢眼媳妇又说话了,他大爷,这家里家外的,以后都是你侄儿的,是吧?余老大想都不想,顺嘴就说,那当然了,这汪肥水,还能流到外人田里?媳妇的吊梢眼里满是笑意,她拿起酒壶,替老大倒满了一杯海之蓝,说到,所以啊,城里的房产证就写了你侄儿的名字,免的以后我们老的走了,你侄儿继承了,还要交这税交那税的。余老大端酒杯的手微微抖动了一下,咂咂厚嘴唇说,中,一家人写谁的名字都一样。几杯海之蓝下肚,老大肠子热起来,他怕弟媳妇、侄儿嫌他,又重新拿了一双新筷子,把盘子里的菜死命往他们碗里夹。老二媳妇又说话了,他大爷,不住城里不知道,这一住下来啊,才明白,城里不如农村好,一天到晚汽车来来往往像过飞机似的,连个觉都睡不好,吃水上电都花钱,连吃进肚里的菜都是污染的。
余老大猛喝了两杯酒,心里比镜子照着还明亮,他把自己给喝醉了。
从此,桑园前的小屋就成了余老大的家。他春种西瓜,秋理发。他对大家不无豪迈地说,一人吃饱全家饱,放下酒壶端茶壶,我余老大过的是神仙日子!
所以,以上赘述,大家就知道,许二鹅的话,是甜里带酸的。
余老大没有把许二鹅的话放在心上,余老大问许二鹅,你家那口子跑回家躲起来了?
许二鹅责问道,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把他吓的晚上不敢在地里?
余老大把自己笑的一声接一声地咳嗽,笑了一会,说,我中午讲古今给那些光屁股孩子听,你家的也凑过来,我知道他是小胆鬼,就添油加醋故意把古今讲的可怕一点,我想试试他的胆子,嘿嘿,他还真是个小胆鬼。
他在自己的凉床上坐了下来。
许二鹅平常闹不明白,自己的瓜园和余老大中间隔的就是一条脚板宽的土埂子,两家的瓜秧能相互爬到对方的田里,瓜的品种一样,大小长得也差不多,为什么人们专拣余老大的瓜买呢?
于是,许二鹅就问余老大的经营绝窍。
我说余老大,你用什么鬼点子,把人都拘到你那里买瓜了?
余老大也不隐瞒,他笑笑说,我啊,随时随地都在卖瓜,给光屁孩子讲古今在卖瓜,给路人说笑话也在卖瓜,给人家修个自行车、理个头发还在卖瓜。
许二鹅和余老大的弟媳妇一样,是庄上有名的两个精明女人,余老大一点,她就心明眼亮。
她黑眼睛在月光下一眨一眨放着亮光。
她笑着对余老大说,我有一个想法,想和你秃和尚商量商量,你看行呢,我们就一块儿敲锣打鼓,不行呢,你只当我没说。
余老大嬉笑道,我们俩还有什么不好说的话。
许二鹅不计较他的煽情,说,你这两天把生意放一放,我们两家伙起来,将打一家。反正你园里的瓜卖完了,这两天,你帮我把瓜园里的瓜也卖掉,卖掉后呢,你开我家的拖拉机去西泰山拉瓜来卖,就说是我们自己瓜园里结的瓜,保证卖的是好价钱,今年西泰山瓜园的瓜便宜,拖拉机的油钱也是我来出。
余老大合计一下说,好主意。这样,我们能卖一个夏天的好瓜!
两家合伙,男人的能力就比出来了。做生意,往往都是一阵一阵的,忙的时候,放个通窍屁也来不及,闲起来让你两眼望青天,双手抱心空空落落。人们像水里的鱼,是一趟一趟的,一趟人过来了,有一个人买瓜,就跘住了一群人,你买一个,他也要买一个,你买他不买,脸上没面子。往往这一群人又招来另一群人。章豆子常常在忙乎的时候,出故障,不是秤杆断了系,就是瓜兜撑破了,人们挤着要余老大秤瓜,余老大忙的汗沿着屁勾流,他一边秤瓜,一边算账,许二鹅在旁边忙里忙外负责收钱找零,余老大和许二鹅配合的琴瑟笙箫,抑扬顿挫。一场生意忙下来,两个人的心里都有说不出的兴奋。章豆子在一边,不是修理秤系,就是重新系秤砣,一副不紧不慢的样子,半天秤了一份瓜,眼珠还要望天翻,算个半天帐。许二鹅当着大众,不好骂他。当一趟生意做完之后,人皆散去,许二鹅就对他扭鼻子挖眼睛,骂道,看你那样子,人家都忙死了,你就是头顶一碗水不泭(洒的意思),闲时你就不能提前做准备?章豆子脾气好,老婆骂他两句,也不生气,他还笑着提着网兜给许二鹅看,看看,这个兜子又要坏了,我还得回家拿一个。
余老大望着章豆子笑,不好说他什么,一伸手从路边拉了两棵土麻,披下皮来,三下五除二打了一个网兜,用力拉了拉,向章豆子怀里一扔说,用它称三十斤重大西瓜,保证你一个夏天拉不坏。要等你回家把网兜拿来啊,这太阳就下西天了。
章豆子把麻兜在手上掂量了两下说,这没有二两重啊,买瓜的不会说我耍奸使赖扣秤吧?
余老大笑着说,我说你这人就是笨屌日死牛,还说牛遭灾。话不是人说的?你那秤不能秤的高一点啊!
老婆许二鹅的眼光,像刀,左瞥他一刀,右剁他一下,懒得跟他多说一句话。
没两天,许二鹅瓜园里的瓜被买的干干净净,剩下的是绿水漾漾的一遍空藤。
章豆子开着拖拉机,余老大和许二鹅坐在后箱边上,拖拉机在路上颠簸,许二鹅的腿就撞上了余老大的腿,余老大就和前面开机器的章豆子开玩笑,你开机器,你老婆老在后面勾我呢。
许二鹅就用拳头打他,打两下,心里感到有一股暖洋洋的感觉。
西泰山离槐树庄不远,开着拖拉机三个钟头就到了,拖拉机下了柏油马路就是土路,由于前两天下了一场透雨,路上稀泥烂浆,章豆子好不容易把拖拉机开到瓜田地头,很担心地说,乖乖,这个路,不说拉一车瓜了,空车我看都不容易出去。余老大听到只当没听到,许二鹅撇着嘴,没好气地斜了他一眼。
余老大见园主是一位矮个子、红脸膛、留着短莊头,走起路来干净利索,是个干家子。他掏出烟来,每人递了一枝,一眼望去,满园西瓜,个体整齐,大小都在十七八斤。令他不解的是,结出这么大的瓜来,一棵棵秧藤却细若柳丝,瓜秧的长度,还不到没有自己的一半长,叶子苍黄成一副病焉焉的样子。他无比困惑地问园主,你这瓜是怎么种出来的?我的瓜秧怎么长的那样盛?园主笑笑,说,你那瓜秧也是瓜啊,不过是不能卖钱的。
余老大见园主为找不到人来采瓜而犯愁,余老大说,莫愁、莫愁,我们仨也算上。于是,瓜园里,采瓜的,挑瓜的,过磅的,忙成了一片。章豆子心里很不情愿,我是买主,我凭什么要给你园主挑瓜?许二鹅心灵,知道余老大的心思,骂丈夫,看见你这死榆木头我就饱了,你尽管挑你的瓜!
余老大是个有心人,他不仅替园主挑瓜,还把地上发现的施药小袋偷偷地收藏起来。
一车瓜很快装满了,园主是个热心人,要求他们留下来喝两盅,余老大说,眼看天晚了,还有几十里路要赶,下次我们就是老朋友了。
园主很大方,给的价是最低的,最后两挑瓜连磅也不过了,只接装上了车。这时候,章豆子才摸到了门道。
拖拉机仍然是章豆子开,余老大和许二鹅跟在后面走,防止车陷,随时准备推车。章豆子开着拖拉机,屁股下放着黑烟,艰难地走了一段稀泥地,前轮打滑,眼看就要停下来,余老大和许二鹅冲进泥水里推,余老大一边推,一边高喊,你千万不能停下来,左右打方向,蛇行向前。拖拉机艰难地放了十几米黑烟,最终还是停了下来。章豆子从驾驶室滚了出来,往地上一坐,嘴里一个劲地往外吐气,这下子完蛋了,我看你们怎么办吧?
章豆子把话说的很不负责任,听起来,好像这件事于他无关。许二鹅没好气地骂他一句。
余老大不慌不忙,赤脚跑回瓜园,请来了挑瓜的一伙人,他自己坐上了驾驶室,开足马力,车子在众人推动下,蛇行前行,一阵黑烟过后,车子走出了那片烂泥地。余老大连连递烟,对推车的人表示感谢。
一连几趟,生意做的很不错。赚来的钱,许二鹅说,一家一半平均分,余老大不同意,说你们两口子又出机器又出人力,我拿了一半,晚上会睡不着觉。我们三人一人一份,你出机器,我出油钱。
家庭过日子,就像唱戏,有主角,有配角。一般家庭是男管唱主角,女管唱配角,这就叫夫唱妻随。许二鹅家和一般家庭倒过来,许二鹅唱主角,章豆子管敲堂锣,这个家可苦怀了许二鹅。许二鹅心气高,苦死累活,家里那一样也不能比别人家差,前年,余老二媳妇盖平房,她非要做个楼基础,余老二媳妇全家进了城,她家盖好的新楼房,儿子说不想要了,想在城里奋斗两年,买个新房结婚,许二鹅拍双手赞成,活人要是活到人家眼皮底下,那还能算活人吗?一年四季,她起早贪黑,做豆腐,压百叶,一村接着一村叫,一大包豆腐叫完了,回来下地还不迟。当然,她也决不可能让章豆子有空闲,闲下来就是撒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没有脑筋赚巧钱,那就让他去赚笨钱吧。她和奶牛场老板讲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凌晨四点至八点,他要去给奶牛挤奶。她在方便袋里装一块烙饼,奶牛场的牛奶管饱喝。自己喝碗豆浆,啃块干饼,就省得做早饭。章豆子给奶牛挤完奶,再拿着瓦刀上工地,一点也不迟。今年春天,她看人家在桑园子里套种西瓜,她毫不迟疑地毁了棉苗改种瓜。儿子打算在城里买房结婚,许二鹅和章豆子商量怎么多余下钱来,帮帮儿子,将来老了,去儿子家住住,心里也硬实。章豆子使劲抹了一把疲倦的脸,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气,眨着满眼泪花说,家里除了你那张人身意外保险单值点钱,你卖我骨头也称不出几斤重量来,他小子在城里有那个命,就买,没那个命就算。我这百十来斤的,你再盘算下去,我怕连上床的力气也没有了。
心气很高的许二鹅,觉的心里有一股凉气往上升,她感到自己很孤单。
唯有一条,她心里对章豆子很满意,那就是床上的事。
章豆子人长的巧小,很像一粒饱满的黄豆。对于床上之事,他也像一粒蛋白质丰富的黄豆,许二鹅手指一弹,他能转着圈儿蹦几蹦,不管白天的活有多苦有多累,他都要回来把许二鹅颠簸的要死要活好几回,上床了一回,半夜迷迷糊糊一回,第二早晨四点钟之前还有一回,家里没有外人,章豆子往往把许二鹅搞的大呼小叫。俩人略作休息,许二鹅给章豆子舀一碗热豆浆,章豆子一碗豆浆喝完,俩人两辆自行车,从奶牛场门前分手,一个去卖豆腐,一个去挤牛奶。
对于余老大,许二鹅起先是没眼看的,一个连外来女人都看不上眼的男人,谁还会把他放在眼里?他和余老大两家,一家居庄头,一家住庄尾,从来不深交。多少年来,她只感觉到余老大这个人,为人处事还不错。
这几天,她也闹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脑子里老出现余老大的影子,余老大笑着在给一窝光腚孩子讲古今,余老大和自己在开心地忙着卖西瓜,余老大一手扠腰,一手夹着香烟在讨教瓜园主种大瓜的经验,余老大身上迎风闻不到别人所说的秃腥味,他身上的味道,是夹杂着烤烟的醇香,有一种让人说不清含义的味道。她有时候会想,老人们说他年轻时候是个俊郎子,他要是没有遇上那场大火,章豆子换成了他,这日子又会变的怎么样呢?
她更闹不明白,自己前一个月还和章豆子在床上要死要活地叫嚣,现在却一点激情也没有了,尽管章豆子还像狼嚎似的,她就像刀板上的一块死肉,任章豆子咬牙切齿地晃来晃去。晃了两次,章豆子感觉不对,问她怎么了?她目光呆滞地说,不想。
哎------有空落只是瞎想想,日月还得糊里糊涂地往前过。
六月天的脸,说变就变。西南天的豹头云,一层接着一层往上翻,河套里的风,突然停息下来,整个世界顿时像肃穆地等待一场庄严的宣判。几粒豆大的雨点,冷不丁砸飞地上的尘土,黑旋风像海里的狂涛,从黑洞洞的西南天卷地而来。余老大桑园里的小屋,像大海里的一片飘叶,在一阵卷风里,被远远地撒到行马河水中,床帐被褥被风高高地挂在树梢上,脸盆锅灶被掀翻多远。没有来得及跑回家的余老大,路边死抱着一棵树根,他一把把许二鹅按在自己的胸前,右手举起一只篮子罩住了头,鸡蛋大的冰雹铺天盖地地砸下来,他失声地对抱着树根的章豆子喊,快拿盆罩头啊!章豆子情急生智,一头扎进路边倒下的树枝里。路上一辆草车,连人带草被掀翻到路边的水沟里,冰雹打在西瓜上,就是小锤打大锤,大捶一个个噗噗噗地裂开来,地上流了一地残存的红水。
飓风疾雨跑马一样地飞过,太阳出来了,支了在树上唱起了懒洋洋的歌,余老大苦笑着对章豆子夫妇说,你们把裂开的瓜装进袋子,送给村里人吃掉,我去收拾家啊。
不一会,章豆子夫妇也来帮忙,许二鹅看着余老大一片狼藉的住处,为余老大着急起来,她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你收拾收拾到我家老屋去住吧,老屋空着也是空着。
说了这话,许二鹅感到脸上有些火热。她带着些许复杂的目光望着章豆子,章豆子正在皱眉咧嘴地揉着被冰雹砸青的腿,她知道老婆在向他征求意见,就顺坡下驴说,到老屋住吧,二鹅说的对,老屋反正空着也是空着。
余老大住进了许二鹅家的老屋,许二鹅又说,你一个人还开什么火做饭,我锅里多添一瓢水就是了,你腾出时间来帮我们家里家外的收拾收拾。
余老大是个勤快人,做事有条理,手脚也不小气,一大早,章豆子夫妇一个去奶场挤奶,一个走东庄去西庄地叫卖豆腐,他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把家里家外收拾的顺眉顺眼。家里缺了荤菜,他隔三差五的不是去集上打二斤肉,就是到河底捕鱼的老荤那里提两条鱼。老荤是外号,是指他爱说荤话,每每这个时候,老荤就会对余老大开玩笑,他说,乖乖,人都说,秃兴,秃兴,你和许二鹅合成一家过了,晚上两个男人对付一个女人,那小女人不是好死了。你当心着下面,不要把老二的毛也磨秃了。
对于这些闲话,余老大早知道是避免不了的,他想,我住她的闲屋,帮他们忙里忙外,吃喝也不让他们上当,是两相情愿的事,白天吃完饭,各忙各的事,晚饭后各去各的屋睡觉,谁也没什么啰嗦,每每章豆子夫妇忙完了早上的事,他早已把瓜摊收拾的有条有理。
余老大的消息,住在城里的弟媳妇知道了,星期天,她牵着儿子的小手回到了村庄。她走到桥顶上,远远望不到大伯子桑园前的小屋,心里泛着不自在,老荤划着小船仰脸望见了她,他们原来都住同村,笑话是说惯的,老荤见了老二媳妇,浑话脱口而出,痒痒了,又回来找秃子性性?他现在不性你了,他去性卖豆腐的那个去了,乖乖,那个豆腐娘子不要好死!
老二家的,用恶话骂了一句划船远去的老荤,拉着儿子下了河堤,向许二鹅家的老屋走去。
许二鹅家的老屋和自家原来卖掉的屋子一样,现在被余老大收拾的有条有理,完全是一副住家的样子。小侄儿非常惹人疼爱,到底是城里长大的孩子,他和农村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这小子一点也不怕人,瘪着腮帮上的两个小酒窝,笑眯眯地叫了几声叔叔,就从小书包里拿出老师奖励的小红花,红本本一样样摆给叔叔看,还搂着叔叔的秃头,偷偷望了妈妈一眼,趴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爸爸偷偷给你藏钱,被妈妈逮住了,钱被妈妈没收了,说是准备给你开个理发铺子,你千万不要告诉妈妈说是我说的。说完,又提过妈妈带来的酒,歪歪扭扭地送到叔叔的面前,说,爸爸给你买的天之蓝。
余老大喜欢的落下泪来,他抱起侄儿,把口袋里的所有纸币,装到侄子的小口袋里说,伯伯使劲苦钱,和你爸一起培养你上大学,你要好好学习。
老二媳妇在许二鹅家的老屋里站了一会就走了出来,她要去许二鹅家当面感谢一下许二鹅,两个精明的女人在许二鹅家门前见了面。
起先老二媳妇站到许二鹅家的门前,许二鹅正弯着腰把盆里的豆渣往桶里倒,老二媳妇吊梢眼里含着满是深意的笑,她站在门前,一声不吭,用这双满含深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忙碌中的许二鹅,等许二鹅突然看到她,被惊的一跳时,她才半真半假地开完笑说,偷奸啦?养汉啦?看把你惊成这样!
许二鹅没有往心里去,手捂着心口,高兴地骂道,你这个冒失鬼,也不知一声,把我魂都吓掉了,快进屋坐。
老二媳妇说,不了,我站站就走,我替他大伯来感谢你,你看他一个男人孤孤默默的,这白里黑里的,就靠你这大弟媳妇照顾了。
许二鹅听她把话说的不清不白的,就疑惑道,你说什么白里黑里的?
老二媳妇赶快笑眯眯地替自己纠正道,你看我这张该掴的漏风嘴,又说错话了,请大弟媳妇原谅,不是白里黑里的,是早早晚晚的。大弟媳妇一片好心肠,我感谢还来不及呢,那能把话说的黑白不分呢。
许二鹅冷下脸来,接着老二媳妇的话说,不是黑白不分,是家外不分,家里不中意的,也能把他扔到外面去。
老二媳妇一听,这话里有话。她扬着一张半笑不笑的脸,接话说,这做人可说不一定,说不定我不中意的,到你这里,你倒很中意呢。
许二鹅说,这中不中意,是要看人心。
老二家的,笑的咯咯响,一把抱着许二鹅的肩膀说,所以,大弟媳妇的心好,我特来感谢你哟。
老二媳妇走后,许二鹅心里一下午都不自在,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和余老大清清白白的,这个余老大往自己的老屋里一住,她许二鹅就成了裤裆里的黄泥巴,如今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说不清的事情,还去说它干嘛?拉下一张脸来,一样话人,你老二媳妇又想在你老大身上打什么鬼主意呢?该当你遇上了我许二鹅,我会让你搬梯子上天------没门的。我把你家老大哐在家里,我不想去讨你老大一分钱巧,我就是要帮你老大拿主张,让你鬼主意得不成,叫你心里比猫爪子掏得还难受,我到底要看看我俩谁是半斤,谁是八两。
拿定主意,许二鹅晚饭多添了两个菜,把夜里替丈夫守夜的叔伯也请了来。余老大把前天老二媳妇提来的两瓶天之蓝打开,一边说着笑话,一边和章豆子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酒,章豆子被余老大两个开心的古今逗的两眼绽开笑花。
许二鹅提起儿子要在城里买房的事。未来的媳妇马上就要显怀了,女方一口咬死,不把城里的新房首付了,俩人甭想枝接连理。儿子胆怯,有些随他爸,前天回家,皱着眉毛,苦着一张小白脸,可把许二鹅心疼坏了,许二鹅筹长划短,左右腾挪,好不容易凑了几万元钱,离首付的房钱还差两三万,他对娘家的大哥说了,娘家大哥让她近两天去拿他的存钱卡。这困难虽然解决了,许二鹅心不甘,他要难一难裆下长着茶壶嘴的丈夫。
许二鹅说话了,卖房钱的还差两三万,前头的大数目,我都跟你想办法凑齐了,这点小头,你章豆子就看着办吧。
章豆子眼皮塔拉下来,心里没有底气,他张开嘴巴要说话,许二鹅掐在这时也张开嘴巴说话,两人异口同声,一个字也不差地说出同样的话来:
你去找你哥转借转借,家里只有那张保单值点钱了。
余老大一转脸,笑的把嘴里的酒吐了出来。
笑过之后,余老大说,哎------都不要难为了,我那里还有一点,你们拿来凑合凑合吧。许二鹅连连说,不中,不中,我和他大舅说好了,我不过想要要他好看。
章豆子眯眯笑道,家里坛子里有多少米,你还没有数啊,尽拿我瞎开味!
坐在一边的叔伯,既不喝酒也不吃菜,光喝水。他们的笑,对他没有一点感染性,他拿起桌上的筷子,狠狠地打了一下蹲在桌角咪咪叫的老猫,怒斥道,你坐在这里算老几啊!就站起身来,独自走出了屋子。
余老大心里一紧,杯里的酒撒了一半。
许二鹅生气地说,他就这样的人,人一老,怪病就多,甭管他,该喝酒喝酒。
初秋的月光皎洁,照出的人影子在地上晃来晃去。晚饭之后,许二鹅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她推出电动车,对已经上床的章豆子说,我到哥哥家去拿钱,明天一大早还要卖豆腐呢。她一紧电门,电动车就开出了村庄,走了很远,能隐隐约约望见娘家村庄的影子了,许二鹅转念一想,哥哥是做化肥生意的,本大利小,手里的周转资金也不宽裕,还不如先拿余老大的用一用,他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着急用钱,等年底手头宽裕了就还他。我好心做好事,还白白为你担坏名,老娘不欠你的!
老屋就在家后头,电动车头一扭就到了。老屋除了余老大,平时很少有人来,院门敞开着,许二鹅走到院子里,听到院东的拐角处有哗啦啦的冲水声,跟着冲水声,余老大嘴里发出嘶嘶哈哈地叫声,叫着叫着,却喊出一个人的名子来,啊------啊------嘶嘶哈哈------二鹅,二鹅,许二鹅!
许二鹅的脸一下子热的像火烧,她想退出院子,可两条腿像灌进了千斤砂子,她颤抖着,迈不动一步,心口像钻进了一只小老鼠,七上八下地跳动着,她一时傻站在那里,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
赤身裸体的余老大像草原上一只饿急了的猎豹,双目亮着邪恶的火光,他像玉米剥皮一般,一下子把白渗渗的许二鹅从绿皮里剥了出来,他咬紧牙关,玩命地嚎叫,嚎叫中带着呜咽,二鹅------二鹅------许二鹅!许二鹅死死咬着他的胸脯,把他的胸肉咬出血印来,臀部努力张开,一挺又一挺地仰合着。余老大在中刀一般的一声呜叫里,轰然倒在许二鹅的身旁。
整个世界死去一般,除了他俩粗重的喘息,什么声音也没有。
你弟媳妇来干什么?许二鹅问。
余老大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她在县城租了一个门面,要我去开个铺子。
你想去?
当然要去,自家的事情嘛。
许二鹅皱了一下眉头,动了动身子。你不能不去?
余老大笑笑,伸手向床脚摸去,他一边摸着一边说,不去,不去我在这里算老几啊?
他摸出两张用方便袋裹好的存单笑眯眯地拍在许二鹅的羞处,说,拿去,手里宽绰了就还我,不宽绰,我就算肥水流了外人田。嘿嘿嘿嘿·····
许二鹅把身子圈成了一个虾米,紧咬着衣角,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的后脊背像筛糠,一下接着一下抖动着。过了好久,许二鹅擦去眼角的泪水,从床上下来,她把两张存单狠狠地甩在余老大的秃头上,疯了一样跑出了自家的老屋。
傻呆在那里的余老大,不知所息,他弄不明白,刚刚还如疯子般癫狂的许二鹅,怎么会突然变成了这样。这女人的心,真是六月里的天,说变就变!
许二鹅骑上电动车,飞快地跑出了村庄,她飞一样地上了行马河大桥,桥桩有两根断裂的地方,许二鹅的电动车头一扭,连人带车栽进了行马河的乱石中。
第二天早上,行马河桥头围了许多人,章豆子抱着许二鹅的尸体哭的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叫你晚上不去你哥家,你怕明天耽误了卖豆腐,非去不可,这以后你叫我一个人怎么过日子啊······
蹲在一边的叔伯说,她不是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吗?赶快向保险公司报案,这是一场人身意外事故。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