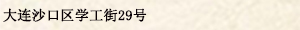清明纸上还乡
还乡记
转眼离开北方已经五个年头了。南京五月中旬以后天气马上就热起来,晚上让人难以入眠,到凌晨四五点钟才能睡着几个小时,等早晨的清新蜕变成中午的暑热,又是一个难熬的轮回。因此,每年夏天一放暑假,我和儿子就逃命似地奔回哈尔滨。
年的暑假,除了避暑,与留守的妻子团聚,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与大姐一起将父母的骨灰送回绥化老家安葬,大哥在南京做更夫,没有假期,回不来。二哥没有买到票,也赶不及回来。就由我代表家里的男孩吧。
7月2号,大姐去长途车站接到了我。从哈尔滨到大姐所在的克山县,需要四个小时大巴的车程。在大姐顶楼的小屋中,我占据了大床,大姐晚上就蜷缩在沙发上,身高一米七十多的大姐年轻时是县里最出众的美女,深夜她蜷缩在沙发上,却显得那么小。朦胧中听见她的叹息,“看你这酒喝的。”是在怪我晚上和同学聚会喝高了。
7月3号,早上起来,站在大姐家的窗前能看见为民湖,视野很好。喝了大姐给泡的几大杯银杏叶茶,醒醒酒。我们要去绥化市张维屯前八村,为父母合葬。大姐先前去过老家,将一应事情安排妥当,我陪着她就行。自从父亲年离开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过去了,母亲比父亲多活了六年,年也脑溢血过世了,母亲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是聚少离多,我很少回克山去,虽然哈尔滨离克山并不是那么遥远。老人能入土为安,算是喜事。
八点半和大姐去克山殡仪馆,取了父母的骨灰盒,装得严严实实,把两个提包四角塞上玻璃丝袋子和塑料布,怕被人看出是骨灰盒,因为当地人迷信,汽车司机不允许乘客带骨灰盒上车。我们先进停车场等着,车来了,就一人拿一个提包上车,放在自己脚前。九点四十发车。大姐有晕眩症,怕车子颠簸,而大巴走的又是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到处是补丁,坑坑洼洼。
七叔家的儿子永春弟弟开面包车来接我们。张维镇属于绥化市管辖,我们的根在该镇的三井乡前八村。七叔是军人出身,身高一米八八,比我还高一点,典型的山东人脸膛,做了二十八年豆腐,远近闻名。永春三十来岁,个子也很高,给人开车谋生,有个儿子叫马彦鹏,样貌和我家马原可像了,也不爱吱声,将来的个子看样也小不了。
翻开我们永字辈的大哥、七十四岁的基督徒马永太珍存的家谱,知道我们的高祖有兄弟二人,名玉贤、玉堂,出于山东登州栖霞县马家营。如今已有后裔十一代,名字分别犯玉、德、坤、文、有、云、景、令、显、永、恒(这一代的名字叫乱了,比如我家孩子就叫了马原,其实应该是马某恒才对)。曾祖父带领五个儿子,来到北大荒,跑马占地,扎下根来。祖父那辈的五个兄弟,只有老四老五有后代,我的父亲马显恒就是老五马德令的儿子。父亲那代有兄弟十人,姐妹三人。我们永字辈也就是我这辈有男女共四十五人。大多分散在本省,新疆有两个,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南京,可能是最远的了。
网上查到了栖霞的相关资料,它位于美丽的胶东半岛腹地,被誉为“中国苹果第一市”。年(金天会九年,伪齐阜昌二年)置栖霞县,年撤县立市。栖霞北临人间仙境蓬莱阁,南近青岛,东北离烟台港、烟台机场仅60公里。栖霞因以“五更平明,海日东升,照耀城头,霞光万道”而得名。作为一座山城,其境内有著名的省级牙山森林公园、艾山温泉等自然景观和绵延百里的十八盘自然公园,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栖霞还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就是栖霞人,“太虚宫”至今犹存。原来我们真正的根是在山东,而且是个美丽的山城,怪不得我和永平大哥都酷爱爬山。
一行亲属一起去前八村老宅,看望六叔显文,八十多岁了,直肠手术后多次发肠梗阻,但头脑非常清楚,说话一点不含糊,记性也很好。他和我父亲最像。六叔的二儿子永水,守在老宅,种地,勉强维持生活。碰见了回来照顾两位老人的秀春大姐和秀凤小妹,还有永臣哥。在六叔家吃了很好吃的芹菜饺子和冰凉的西瓜,应该是用井水冰镇的。小时候我们常把黄瓜洗净,放在大水缸里,黄瓜经清凉的冷水浸泡,又水灵又爽口,我会偶尔扒着比我还高的水缸,去看碧绿的黄瓜浮在门背后阴影笼罩的水面上。
晚上我们住在七叔家,傍晚没事,又去大舅家院子里摘树上的樱桃吃,刚刚被雨洗过,樱桃通红、干净。北方的樱桃很小,不像南方的大樱桃,只比黄豆粒大一点儿,里面的大籽儿包着薄薄一层果肉。一开始稍微有点酸,吃一会儿就不酸了。乡村雨后的黄昏,站在树下边摘边吃,可以把樱桃籽随便吐在树根下。抬头,能看见村外的大杨树簌簌颤抖,反映着最后的余晖。大舅的房子带有很长的院子,里面种了有十几种蔬菜,茄子豆角黄瓜柿子韭菜大葱等,除了三棵樱桃树,还有李子树、沙果树。房子买下来才不到三万元。七叔家也有园子,也种了菜,养几头大猪、鸡,一条狗叫“傻子”,据说只要知道是老马家人就不咬,确实,第一次进院,它还叫,后来就再不咬了,而大舅每次来,它都蹦高高咬。现在的七婶信主,很勤劳。屋檐下的麻燕子窝里,早晨传出来小燕子咻咻的烧火声。老燕子看见有人站在门口,就停在晾衣绳上不安地叫,看我不走,就猛地飞掠过来,特意向我的头顶俯冲,靠得不能再近时才一掠而起。
7月4号。在七叔、永春、永太、绥化赶来的五哥永福、永水及风水先生和几位司机师傅的帮助下,虽然头天晚上雨下得很大,地里都是泥泞,我们一个面包车、一个半截子加一个手推车,终于将一应物件运到了家族墓地。墓地周围都是田地,一望无际,绿油油的,充满生机。五位祖父的坟都在那里,大爷爷的骨殖还在南头的老坟地,此处是他的影子坟,曾祖父的坟也没有迁来,那里已经被平成了耕地。之所以没有动曾祖父的坟,是因为那里的风水好,子孙人丁兴旺。当时管家的三爷爷就说,“有人就行。”结果,老马家真的人丁兴旺,虽然没有出做大官的,也没有经商很成功的。我这辈之后,不少人都考上了大学。大庆研究院的永义在俄罗斯拿了硕士。我算是学位最高的,读到了头。永福的两个女儿都在绥化的重点中学,教数学和语文。其他的情况还不了解。父母死后,似乎和亲戚们的联系就中断了。
早上七叔领我去风水先生家,抓了只公鸡,给铁锹上抹点血,第一锹土是我挖的。我给泥瓦匠递砖,墓修成长方形,里面都抹了水泥,放了铜钱,上面放馒头,再把父母的两个骨灰盒放上面,用灵幡盖上。我还以为要把父母的骨灰放在一个盒子里呢,结果还是按照原样,每人一个骨灰盒,放在同一个墓穴中。我觉得父母还是有点孤单,为什么不能把他们的骨灰参在一起呢。我对丧葬的习俗可谓一窍不通,也不敢多问,只是觉得父母还是分开着的,就像住在一所房子的两个房间里。碑是黑色大理石的,很漂亮。我蘸着矿泉水把碑擦得亮亮的,知道妈妈喜欢干净。完毕后,我和永春挖了三车黑土,把坟墓四周培上,顶部留出来,四四方方的。各个家族死者的坟墓上都烧了纸,给妈妈烧了好烟,祭洒了白酒,各色供果码在墓碑底座上。圆坟是不准哭的。因为风俗的原因,大姐只能等在村里。我也不许哭。
回去的路上,车开出很远,回头望望,父母坟墓前的碑还可以醒目地看见,缠着红布,好像是爸妈在张望着自己的亲人走远。随着车越开越远,那黑色的大理石碑显得越来越高,高过了那片地里的一切。家族墓地还有很大一片地方,我和叔叔说,我以后也葬在这里,不然就得把骨灰洒到江里了,那就彻底地漂泊无着了。和爸妈在一起多好啊。爸爸年参军离开这里,经过了六十四年才回到故里,爸妈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我们做儿女的也安心了。回到镇上,在鑫新园饭店吃饭,我陪大家喝了两玻璃缸子白酒,结果睡了一下午,晚上起来吃倭瓜,然后又一直睡到早上四点多。
7月5号。早上看七叔做豆腐,豆子要泡六个小时,磨碎,出豆浆,加热成豆腐脑,用洗衣机搅,用棒子缠着十几米长的布,铺在长方形的木头槽子里,铺一层布就浇一瓢豆腐脑,再压上布,再浇。晾干之后就成了干豆腐了。大豆腐冬天才做。七叔要从凌晨四点干到八点,出去卖,不到九点就能卖完。他转业回来时起初在粮库扛麻袋,后来想起做豆腐,干了两年就盖了现在还在住着的房子,当年算是镇上比较好的房子了,二三十年也没有大修过。叔叔给我揭了贼香的豆腐皮,洒上椒盐,太好吃了,我勉强全部吃掉了,因为实在是太香了。
这一天没有什么事,我和大姐商量,去绥化市里玩玩。七点的客车,一个小时就到了,市里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到处是人和出租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片灰白色,似乎没有色彩。打车去了地藏寺、城西的一个寺庙和基督堂,基督堂里祷告的人有几百人。庙里有念南无阿弥陀佛转圈走的和尚与尼姑。回张维镇的途中路过父亲当年做总指挥的引嫩工程的原址,黑鱼泡,有一年我在那里待了一冬天,吃奶糖吃得小脸溜圆。父亲常常组织夜战,堤坝上拖拉机的履带压在砾石上,爆出一连串的火星子。我一个人留在屋里,父亲怕我害怕,就让我抱着一杆没有子弹的步枪睡觉。小时候的风雪总是很大。还记得营地附近的小河,头一天我和另一个小朋友会跑去凿出一个冰窟窿,第二天早上再去,用棍子捅开冰窟窿上一夜结出的薄冰盖,由于压力的变化,小虾会一个个从水中蹦到冰面上,我们就用一个盘子拣,拣了足足一盘子,回去在营地的厨房里让师傅炒得通红的,用手拈着吃。
7月6号。上午还有一个简单的仪式,给父母的坟“上梁”,然后就再没什么事了。大姐、我、七叔、永春先开车到前八,又去看望了六叔六婶,都八十多岁了,给叔叔扔了点钱儿,永水哥的妻子跑到园子里摘了几根小黄瓜,味道像村妞儿一样纯,北方人管没长成的小女孩叫小黄瓜妞儿,这种小黄瓜妞儿用来腌咸菜最好了。看到邻居荒废的房子和前后两个大园子,起了想在老家买个平房的念头,托七叔在镇上给打听打听,这样我每年回乡祭祖也有个窝,平时他们谁爱住谁住,可以帮我种种菜,夏天回来看青儿。农村的好处是自己种的菜够一夏天的了,只有冬天四个月需要存菜、买菜、腌菜之类。如果以后再安装了下水,那就方便了。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了,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妇幼,村子里显得空寂,只偶尔有几只鸡在村路上来回踱步,带着思考的样子,不时叫上几声。
我们把车开到离坟茔地最近的地方,再往里道路泥泞,车会陷住,我们便步行前往,踩着油黑溜滑的垄沟,我扛着三根苞米秆,其他人拿着烧纸。父母坟前的供果还是好好的,葡萄上爬着蚂蚁,我扭下一颗尝尝,很甜,大姐吃了半截香蕉,都说吃供果好。把玉米秆在坟上弯成弓形,固定住,这就是“上梁”了。新坟不能高过旧坟,所以父母坟墓上面还没有覆土,四外圈的新鲜土上已经有蚂蚁团出的小颗粒了。给墓地里的每个坟头又分别烧了纸。我和大姐给父母磕了三个头。据说不能掉眼泪,否则父母的屋顶会漏水。这就算完事了。三年后再来上香。其实我每年回北方避暑,就可以来父母这里看看,坐坐,在心里和他们说说话,或者只是坐坐,感受着田野里的风吹,吹过辽阔的大地,一直吹到来世。家族的墓地很大,我估测了我以后要占据的位置,挺好的。谁都要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的。爸妈终于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了,我们也有了根的感觉。大姐说以后也要归到这里来,几个亲戚说不可以,只能葬在墓地边上,大姐说,边上也行啊,只要能望见爸妈。
回到镇上,赶上了中午的大客,与大姐一起回克山,一路顺风。下车又吃家常饼和葱花饼,吃土豆倭瓜。晚上与同学欢聚,留在克山的小时候同学大多都熬了个官做,劳动局局长、社保局局长、人事局局长、工商行行长、户政大队队长、乡党委书记等等,一大堆。见到了小慧的堂弟小凯,他的散文写得很好,可惜现在太忙,只能写日记,用旧流水账本写,写了有两尺厚了。我的诗《小慧》中写到他,这次具体了解到小慧去世时是二十八岁,是白血病。小慧比他大一岁,小时候我们仨关系很近。半夜回到大姐家,姐姐还敞着门等我呢,脏衣服都洗了,挂在窗前。下大雨了,雨落在只剩下一个亲人的故乡。
7月7号。早上与大姐在为民湖(原东大泡子)溜达大半圈,又去了爱民湖。看了爸妈留下的老房子,现在属于二哥,门锁着,从邻居院里隔着板障子一看,满院荒草已经几乎高过了屋檐,密密实实的。院子里的樱桃树上果实累累,我折了两小枝拿着,准备回姐姐家插在她插竹子的花瓶里,放在电脑旁边。我们姐俩在泥泞的大市场吃烧饼,喝麦米粥,芹菜叶咸菜。我吃了两个半。买了当地的香瓜,拎着,溜达到城西北的永安寺,听听佛号。然后和姐姐一路又溜达回家。
风一吹,杨树叶子就翻出背面的银白色,我和姐姐走在泥泞的路上,扛着樱桃树枝,我们偶尔说话。仿佛父母还在那一片田野里站着,望着我们,无论我们走得多远,他们都能看见我们,只是他们不再和我们说话了。夏天很快就过去了。这已是一年前的事情。我已经打消了在老家买座平房的念头。
年4月19日
北京白癜风医专科医院白癜风哪里治疗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