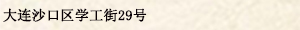瑞英实力派杨成菊
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
近日公司组织学习了《把信送给加西亚》这本书后我们才顿开茅塞,这不愧是一本风靡世界畅销全球催人励志的好书。该书的作者用富有哲理的语言和敏锐的洞察力,向当今的世人展示了由主动性通往卓越的成功模式的具体执行者—罗文的雄才大略。人们在佩服成功者同时也在感谢成功者的推荐者,因为他知道罗文是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合适人选。这本书的精神实质就是挖掘罗文那种不负众望的进取精神。
当一种临危受命即将要去执行的时候,向上级推荐了合适人选的这个人也是值得称赞的,他的准确无误的荐举不但使国家的危难得到了挽救而且使出色完成任务的加西亚有了用武之地,从而使国家从危难到获得胜利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英雄的传奇色彩。试想我们企业现在的发展何尝不急需这些能发现人才、知道利用人才、会培养人才的人才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对比一下,我们跟罗文的差距在哪里呢?
作为企业员工的一员,也要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企业改革的脚步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所在,企业的市场潜力就是企业未来发展的全部,其中的发展探索过程就需要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来实现,只有找准各自的位置才能在各自的岗位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便达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素质,最终完成企业所赋予的历史使命。现在企业的市场竞争时代也是挖掘员工个人潜能的时候。
面对企业发展现实我们一直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却从来没有想过谁该去铺就通向成功的路,现在才深深意识到这铺路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但要做这铺路者而且还要知道在哪里铺路最有希望通向成功。前人一个世纪以前的英雄壮举,我们今天用来学习指导企业实践虽然晚了一点,但是总比没有认识的好,现在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知道了该如何努力去做。设想一下,如果企业需要员工去完成一件非常难完成的事情,我们具备不具备被推荐的能力,如果我们就是那被推荐出来的“罗文”,在企业现有条件下,我们能否每个人都能胜任?
很欣慰就在我们对企业发展的市场缺乏深刻认识的时候,公司适时推荐了这本书作为我们工作中的行动指南,不但从精神上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而且在道路上给我们树立了楷模。使我自己也更加深刻体会到,企业发展到今天更需要不断用智慧武装自己,知识是无止境的学问是边缘的向导,每一本好书都可能给予我们一个提示,每一种技能都能丰富我们的头脑,谁掌握了这些谁就能把信成功送给加西亚。
我的土气特质
没有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土气,更没有人愿意听别人说自己没有层次,我也一样。但是我确实有时土得可以,有时候也层次得可以。土的时候是听别人说的,层次的时候是自己感觉的,但大多数我是游走在两者之间,这也是我自己感觉的。
我家祖祖辈辈的确是农村的,父辈从青年开始才脱离了农村到城市里居住,然而他农村的底子很厚实。我真是在城市里出生的,可是却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我接受的教育全部是城市的。
虽然是等到上学年龄才回到城市,可是直到高中毕业以前还一直想念着农村的亲人和热土,各个假期都希望去老家那里度过,也就是城市一学期农村一假期。所以那段光阴我也一直在农村、城市之间挣扎着情感,土气的时间不多但也总是挥之不去。
工作半年以后,才深刻意识到城市情结的重要性,就买来牛仔裤和带跟皮鞋把自己装扮起来,尤其头发只烫个留海儿更多点儿城市人的特征。特别是我农村最亲的亲人逝去后,农村的故土也不那么牵挂了,就开始融入城市夜景的繁华了,有时侯甚至也能塑造街边一景。
这么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积累以及知识阅历的积累,心和骨子里一直执著着一个真理,被土气的外衣包裹着的我从来不觉得特质有什么不好,至于特质到什么程度也说不好。不过也憧憬着穿上高档服装的雍容华贵,可是一直也没舍得用一年的薪水实现这个愿望。只能是几个月或者一年,才咬牙买来中档衣服穿得稍微得体一些,大多数时日都是穿着公司制服上班,并且到处不讲究地溜达到亲属家。
一般说我土的都是我的同事和亲属,他们经常见到我的是十几年不变的穿衣方式,因为公司制服设计方案一直没改变多少;感觉我有档次的则是我的同学和朋友,因为一般都是有准备情况下去跟他们见面,就是把平日不舍得穿的衣服拿出来换上张扬自己。即使偶然被他们看见我穿制服的样子也羡慕着说,你单位效益真好,制服都是名牌的,显得你挺有气质的。其实我是知道,大公司设计的品牌制服就是必须要保证高矮胖廋穿起来都好看的,即使不是标准体型也都是量体裁衣。
虽然我不完全承认自己的土气,但是洋气绝对算不上,跟农村人在一起仔细瞅两眼才能发现也许与众不同,跟城市人在一起大部分时候不显眼,有时候挺显眼,显眼的时候就是显出了土气特质。确实,我最惬意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穿着最随意的时候,每次要是出去把自己约束起来跟着流动趋势,那一天会很累的。
老家房前屋后消失的小河老家,我已经离开多年,确切地说,我是在年夏天离开的,那年我七岁,当时是为了回到城里上学,可是我很不情愿,死活都愿意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可父母不那么认为,他们觉得我应该回到城市里读书,城里的教育资源更好,况且城里的家附近的小学是区重点学校,师资力量以及配套设施都比较好,就硬拉着我回到了陌生的城市。
我走之前,我还跟村里的玩伴都告了别,至于剩下谁没通知到,我也都忘记了,我想等我走后,她们都会马上知道,并且她们会很想我吧,因为我一直很想她们的。我清楚地记得,我走的时候,爷爷奶奶身体还算可以,除了年长一些外,在那整个村子里也属于年长的,其他的我还没感觉会很快相继离去的。我还记得,老家的房前屋后一共有三条小河儿。
西南边的小河儿相对比较来说算是最大,也离奶奶家最近,出了院子,往西一拐就是一片苞米地,苞米地的尽头就是,小河从这边望不到对岸,里面夏天有茂密的水草和小鱼儿,哥常在那里用捂子捂鱼,鲫鱼和泥鳅居多。大孩子们可以随意去那里游泳,我却不敢,哥看着我也不让我去,说是我自己一下去就会被淹死。跟他一起去的时候,也就是让我在岸边坐着看着,只可以把双脚耷拉在水里一会儿就得,然后就撵我到岸上的碾盘上帮他看衣服。那碾盘直径能有3米,爷爷说那是早年生产队用来碾米用的,至于怎么碾米我从来没看见过,也好奇中间怎么那么大一个圆窟窿,有脚能伸进去那么大,我们一般在上面玩泥巴的时候还得避开那地方。四周没有树,种满了庄稼,庄稼品种种得很单一,不是高粱就是苞米,没有一样是我爱吃的,那时候还不舍得都掰青苞米吃了,而我就仅仅爱吃青苞米,所以我对周围大片庄稼的兴趣完全没有瓜地那么浓,想看瓜还得去村东边村里的瓜地。
河里那些水草水上部分也有一人多高,采摘上面的嫩穗可以吃,不是怎么好吃,吃不吃都行,估计乡下能吃不能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毒吧,河面上的两种水草也有可以吃的是它的根上有种子,这个确实可以吃,叶子像袖珍荷花一样水面上浮着,把它的梗抓出来,扭下根下面的种子然后再扔到河里就行,说是能继续生长。现在都好多年不见了,我确信我还能认识它们,是跟西南边的小河一起认识的,在以后的各地的小河里没有再见过。我一直记得它们的名字,但是至今也不知道那些字怎么写,或者学名叫什么,有机会真得仔细查查。很奇怪的是,西边这条小河的南边原来的低洼处居然不知道啥时候垫起了土堆,哥说那叫房身,然后就盖起了房子,一户人家就搬来住了进去,跟原来那村子两趟房不在一起,就那么孤零零地存在着。平时有大地里的庄稼挡着看不见,等一到做饭时候,那里也跟着冒起了炊烟,现在想想,原来村子里的两趟房旁边由于有河的缘故,没有多余的地方扩展了,那户人家是另起一行的,也算是外来户的坐地户吧,不跟大家一个姓,这个村子是个姓氏村。
我听哥的话也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不让下西边那条小河,我却常跟伙伴儿去后边的小河,并且有一次真差点儿淹死,那时候要是淹死也就死了,也就没有后来这么多废话了。后边的小河跟奶奶家隔一趟房,前后趟房中间是一条不宽不窄的小道儿,可以赶马车过。穿过后趟房谁家或者是绕一圈,就可以到后面的小河儿边游泳去了,我总是主动去找那些有的叫姑有的叫姐妹的去玩。在她们的鼓动下,我也半会半不会地学起了游泳,就是把脑袋伸进水里的狗刨儿,另外两个可以互相摁着脑袋在水里玩,我不敢去按她们,因为我自己都是勉强保证不沉下去,但其中一个却过来把我按了下去,我咕嘟咕嘟地喝起了水,呛得够呛,要不是我拼命挣扎估计那个夏天的那天就没了。我在水里一直说着:烦人!烦人!她们居然还笑我,因为烦人这词的确是一句城里话,那是我回城上学的第一个暑假的时候。
后边小河给我的记忆,除了差一点淹死外,就是挨着后面小河的几户人家也比较陌生,陌生的大多数是外来户,但是尽管陌生,挨家挨户我也都去过,他们家都没有跟我能玩的伙伴,有的都是老年人,也就是我得管叫爷爷奶奶的,有的是我管叫哥哥嫂子的,他们的孩子都很小。可是我还是不知道当时怎么想,居然每家都去串过门,有的还吃了人家烀苞米、烧土豆啥的,尽管奶奶多次告诫我,人家吃饭时间不能去串门,谁家给啥也不能吃,别让人家笑话,尤其是个丫头,更不能馋嘴。我还真没管那个,到了谁家没个准点儿,半拉苞米面饼子吃得也挺香,有的人家还放了糖精的,更好吃了。他们那些人家对我也都很友好,知道我父母在城里,也知道我是谁家孙女、谁家女儿。还有的我最不爱听的话也时常从他们嘴里冒出来,说我如何小时候里吃过谁谁的奶之类的,的确是有那么回事儿。
我八个月大的时候,父母把我从城里扔给乡下的爷爷奶奶抚养,奶奶开始就是抱着我挨家挨户找人给我喂奶,我也就吃遍了那里的同龄人妈妈的奶了,奶奶的意思就是吃一口得一口,促使奶奶常常抱我去讨奶的原因就是,那时候我长得大脑袋小细脖地,怕不好养活。可是谁要是说我大眼睛双眼皮儿挺好看,奶奶就很高兴,谁要是事实求是地说我有点对眼儿、还奔儿楼瓦块地,奶奶就不愿意。我的头发还稀拨愣登地黄,想扎个小辫子都勉强。怪不得那个小伙伴敢把我按水里,估计是不怎么待见我,并且我又生性软弱。
其实跟我在后边小河里游泳玩的根本不是我最喜欢的伙伴,我最喜欢的伙伴还是东街的几个,就是家住在靠东南边小河边的,我都得叫这姑那姑几姑的几个人,她们一家一般都有几个孩子,大孩子们通常也是跟我几个堂兄弟姐妹一起玩的,小的几个跟我玩儿。我跟着她们到处跑,东边除了有村委会,还有小砖窑,再有就是一片日夜有人看着的西瓜地和香瓜地,整天看得很紧,跑不快的根本不敢去那里踅摸着啥,周围也不封闭,就那么让人眼馋不敢动。我能借光的时候,就是大孩子们偷完没熟扔下不要的小瓜蛋儿,有的甚至是被咬了一口有些苦的,我也要来翻个面再啃两口尝尝也咽了下去。除了玩以外的大部分事情都与我无关,每次我出现在大人们面前,他们都会提起一下我的父亲,父亲每次回乡下也都各家拜访拜访加深印象,而且还不忘嘱咐他们,说我在那里希望多多关照,意思就是别让他们家孩子欺负我。即使被人欺负了我也不好意思说,好像很没面子一样,一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奶奶呢,是个小脚,走哪里都不方便,我也挺不理解别人怎么不能帮助一下奶奶呢?比如别人家树上的桃子、李子、杏子成熟了就不能多给咱几个?开始也挺纳闷,家里的园子怎么就不种几棵果树呢?那样的情景多好啊!后来听大伯说,家里人口多,全靠园子里的地方种些蔬菜维持生活,要是园子里有果树的话,就欺得庄稼不爱长。我还是想,哪差那一块地方种那破白菜啊。那就顺其自然吧,也有一次用土块砸了一个远房堂弟,听着他疼得嗷嗷哭的声音我愉快地跑远了,头上两个旋儿的他的确欺负了我好几次,最可恨的一次是他把我推到东边的小河里的,我自己扑棱扑棱爬了上来,一身泥水哭着回的家。
从那以后,奶奶不让再去东边玩,怕再遇到他把我塞河里出不来。那个夏天我都乖乖地待在西边,出门远远看见他也很快躲回屋,仿佛整个村子东边都被他霸占一样。直到冬天来临,河水都冻住了,我才有机会再去东边看河。去的时候冰面正被村里人刨开一个大洞打鱼,还不让小孩靠近,怕滑到冰窟窿里去。我就远远在站着,看着本来活蹦乱跳的大鱼小鱼一条不剩地被他们捡走,然后被上称挨家挨户按照人口分下去,自然分啥也没有我的份儿,分猪肉也没有我的份儿,我户口不在那里,也有人看见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口头安慰了我。
随后不久我在当地上了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跟着姐姐们去,学的也不咋地,所以才回到城市来上学,可是还是很想那里,想爷爷奶奶,想大伯一家的兄弟姐妹,也想西院的堂叔家的兄弟姐妹,甚至也想那个远房的堂弟。原来班里的同学也是记得比较清晰,而且现在我还能记得其中一部分同学的名字,就是不知道他们记不记得我了。回来正式上学以后,学校里的教学资源真的如父亲所说挺好的,可以参加各类学习比赛,我雨天鞋子、裤子都湿透了也在答卷,得到的奖品除了奖状就是本子和笔,也就几毛钱的东西居然很高兴。每次放寒暑假也许会有机会回老家看,爷爷奶奶都老了很多,由于思念我的缘故,都病了几次。西南边、东南边、后边的小河也都陆续被填平,盖上了房子,现在的三排房子的村子人口也增加一些,搬来了一些外来户,我也再没有机会去认识他们了。再后来,爷爷奶奶、大伯等长辈们又相继离世,我都没能有时间一一去送别终成遗憾。
近些年时间充裕了写就时常再回去,大部分去也是因为平辈的兄弟姐妹们家中的大事小情了,他们首先就会想到我,而我也是趁此机会再看看家乡周围的一切。变了,变了很多,茅草房也没有了,都是镶嵌着琉璃瓦的砖瓦房了。马车偶尔有,家家都有农机具,农用车、自用车也很常见,院子里屋檐下也都是水泥铺就,都留着对开的两片园子,院子里都至少种着棵果树,春天满院子的花,秋天满院子的果实,这样子才是我很小那时候希望看到的景象。而乡亲们的家里又都剩下了老年人看家种地,年轻一点的也都进了城市,偌大的三间瓦房都显得宽敞明亮,一个大炕睡几口人的情景是历史了。还发现不单是那三条小河再也没有了,那个大碾盘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桑葚故事到了吃桑葚的季节,街头巷尾的水果摊上都有卖。有时候我会买上一些,回来赶紧吃,因为熟透的桑葚放上一会儿工夫,就会有紫色的果汁渗出扔了太可惜,只有把果汁的营养吃进肚子里才放心。现在的桑葚果粒儿都比较大,也不知道都产自哪里,或许是品种的问题,也或许是产地的问题,跟我小时候看见的不太一样。
上学前,我在老家生活过一段日子,所以也了解一些农村事物,其中就包括桑葚。那时候,桑葚在农村也不是很常见,常见的都是些杨树、柳树、榆树。认识桑葚还是在离村子七、八里地的地方,在大队的西南角儿,有一片圈起来的桑林,轻易不让外面人进去。回家跟奶奶说,奶奶告诉我是那养蚕的地方。还告诉我,那树上结的小果子长成了就好吃,那小果子叫桑树粒儿,大小跟榆树钱儿差不多。这些话我就一直记在心里,总想找机会去看看。
一是想看看蚕是啥样,当时我以为蚕就爬在树上。不久以后爷爷特意领我去了大队饲养场,才知道蚕是养在大笸箩里,像大绿虫子一样蠕动,然后需要摘下桑叶去喂它们,所以那种蚕叫做桑蚕,还说桑蚕吐的丝叫桑蚕丝能做衣服。再者就是我还想看看桑树粒儿,更想亲口尝尝那果实啥味道,当时想着是不是也很甜。
等那个夏季来临的时候,终于有机会跟小伙伴们去采摘桑树粒儿了。站在不高不矮的桑树下,我只有仰头看的份儿,连最低的枝条都够不到,就在树下看着他们爬树摘。桑树粒儿没成熟的时候是绿色的,等熟透了才变成了紫色。桑树经他们那么一晃,偶尔会有紫色的掉在地上,我就高兴地捡起来,酸酸甜甜的很好吃,所以就希望能多掉下来几粒儿。
其实经过各村子里人的采摘,树上桑树粒儿星罗棋布地不多了。时间不长,大队出来人就把我们都撵跑了,有的也顺手掐下带有桑树粒儿的枝条边走边吃,等他们要扔的时候,我才要了过来,因为上面还有几个未成熟的也能吃,就是没啥味儿。
读书以后才知道,桑树粒儿学名叫桑葚。等再过些日子,我也会专门寻找家乡那种小桑葚,买来吃吃感觉味道似乎是更好。
作者简介Authorintroduction杨成菊,中共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沈阳作家协会会员、鞍山作家协会会员、鞍山诗人协会会员、鞍山诗赋协会会员、鞍山网络作家协会会员、鞍山诗词学会会员。通信工程师。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勤于笔耕,并已数次获得相关奖项,一次获国家级奖铜奖。其中诗歌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铜奖、鞍山市首界人口文化突出贡献奖、鞍山市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散文曾获鞍山地区庆国庆征文一等奖。论文多次获得辽宁省通信行业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