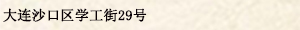韩月莉怀念六一
怀念六一
文/韩月莉
今天我们广场舞队的队长燕飞老师在群里说,“六一”表演节目的时候要统一服装,姐妹们你一言我一语都纷纷表示赞成。随着这个话题的结束,我回忆起了童年的“六一儿童节”,那些记忆仍旧是那么的清晰。
棒棒鞭儿、花环、纸花儿、腰鼓、粉花布衫儿、白布衫儿、蓝布裤、红绸布条儿、粉绸布条儿、黄绸布条儿、抓角儿和羊角辫儿……还有糖大饼,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个年月,大人孩子都没有花钱的意识,过“六一”用的道具基本上都是家长给孩子做的。
棒棒鞭儿是用比扫帚把细点,长约2尺3的木棍,在木棍两头凿孔儿、串铜钱儿,再在两头扎上花布柳条儿穗穗儿。花环是用柳条儿圈成圈儿,用彩色纸剪成花芽条条儿,把花芽彩纸条条儿缠粘在柳条儿圈上。做纸花最好的材料就是带皱纹的绸绸儿纸,或者用一面有色的彩色纸做。最先进的道具恐怕就是腰鼓了。教我们打腰鼓的是杨智老师,他是平反后被分配到我们麦子疃学校的。杨老师不但讲课好,而且多才多艺,唱歌、跳舞、乐器样样精通。为了丰富学校文体活动,杨老师建议学校购买了腰鼓。
每年“六一”表演队的女孩儿上身穿粉花布衫儿,下身穿蓝布裤;男孩上身穿白布衫儿,下身穿蓝布裤。这是教练老师的一贯要求,也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服装。那时候女孩儿留长辫子的多,“六一”那天老师要求都打起抓角儿。
我记得那时我一年起两次五更,一次是过年,一次就是“六一”了。“六一”这天家长们兴致也很高,五更起来就给孩子做饭,而且是捡好的做。有烙饼的、有拌旮瘩汤的,家里没有白面的,也要给孩子炒上一碗小米饭,在那个年月,这些就算是好饭了。家长们打发孩子吃完饭,开始换新衣,梳辫子、扎绸花儿,忙的不亦乐乎。孩子们吃饱、换上新衣服,便兴高采烈地到学校化妆。
化妆完毕,整队出发,到南杨庄中心校表演。同学们一路上敲锣打鼓,边走边表演,用高亢嘹亮的声音,整齐地欢呼着:“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热烈庆祝六一儿童节……”那欢呼声响彻整个村庄,响彻三里五村。各个学校的表演队在路上撞见,就开始较量。但是直到正式表演结束,麦子疃学校,我们的学校始终是第一!
麦子疃村人杰地灵,自然资源在方圆几十里也是独领风骚。麦子疃村方圆十里的果树坡就让人倍感诱惑,每年杏熟的季节和果子成熟的季节,总会吸引来许许多多垂涎三尺的亲朋好友。
麦子疃的部队营房也助长了麦子疃人的威风,村里人沾了部队不少光。就说看电影,那时没有电视,电影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驻地部队隔三差五给村里送去电影慰问村民,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村里人还能从部队服务社买一些地方上缺少的生活用品。我还记得部队的贺军医经常下村给老百姓看病、治病。
麦子疃还有自己的戏班子,我记得戏班子的班主杨喜弟舅舅经常逗我说要买我的长辫子,还拿一块钱的“大价钱”诱惑我把辫子卖给戏班子。那时候,麦子疃村每年正月唱大戏,一唱就是半个月,白天唱完,晚上唱。人们穿着新衣服、嗑着瓜籽,悠闲地坐在戏台下面看大戏,那真是麦子疃人的福气。
麦子疃的地性是沙地,种出的西瓜、菜瓜、香瓜,香甜可口。麦子疃村的优势多多,难怪南杨庄公社(现在叫乡)流传了一句顺口溜:“东北江、南杨庄、麦子疃是个好地方。”我虽然只是麦子疃村的姥姥家,但是,我最纯真的记忆都留在了那片瓜甜果香的热土上。我始终把麦子疃当做我的第一故乡。麦子疃的姥姥、舅舅、兄弟姐妹们也没拿我当外人。我已经三十多年没在麦子疃生活了,我的发小们至今也和我说:“咱村谁谁谁,咱村如何如何。”咱村俩字让我听着倍感亲切!
我对小时候的“六一儿童节”有着特殊的怀念之情,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出尽“风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我们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我们要快快乐乐地度过这美好的时光……”每年我都会朗诵这几句经久不衰的开场白。以至于后来开幼儿园,我又把这几句开场白传给了幼儿园的孩子们,只是把“少年儿童”改成了“小朋友”。我记得原来这几句“开场白”不属于我,是初中一年级杨林香大姐姐的专属。我记得杨林香大姐姐长得相当漂亮、大方,而且聪明,学习又好,是南杨庄公社出了名的好姑娘。
我记得我念二年级时,有一次我正在校园里和同学们玩,张万礼校长突然叫我到办公室。张万礼校长长着一张包公脸,留着大背头,很少笑,我们那时候觉得特别怕他。当时虽然他是带着笑容叫的我,我还是怕的够呛。进了办公室看到杨林香大姐姐在朗诵一段话,对内容我理解的很少。张万礼校长让杨林香大姐姐把那段朗诵词教给我念。杨林香大姐姐并没有嫉妒我要取代她,而是认真地、一字一句地、亲切地教我朗诵。我感觉到姐姐很喜欢我。可是我认识的字太少了,那时二年级学的字未必有现在幼儿园中班学的字多。杨林香大姐姐教我念了好多遍,我愣是没有独自把那段朗诵词念下来。后来张万礼校长说:“孩子太小了……”然后笑着摸摸我的头,对我说:“耍去吧”。我记得当时因为自己不会念那段朗诵词,很害羞,满脸通红地走出了办公室。后来随着我的长大,杨林香大姐姐初中毕业到南杨庄公社念高中以后,那些报幕呀、演讲开场白呀等一些露脸的事基本成了我的专属。
那时候每年“六一”演出结束后,都给同学们每人发两个糖大饼。那糖大饼甜甜的,至今都令我回味无穷。因为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一年当中恐怕也难吃几个糖大饼。在我的记忆里,糖大饼的味道是过“六一”的味道之一。那时候的我们虽然年龄小,但是都很懂事,也很有爱心。表演结束,已经是下午一两点了,已经很饿了,再加上糖大饼的诱惑,本来两个糖大饼谁也能吃完,但是我们每个同学都只吃一个,剩一个留给没上学的弟弟妹妹吃,留给爹娘尝尝。我和姥爷姥姥虽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但是我也要剩一个给姥爷姥姥尝尝。因为我觉得过“六一”发的糖大饼格外的甜、格外的香。每年“六一”吃完糖大饼,在我们的心里也就算给这一年的“六一儿童节”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近几年,中老年人过“六一儿童节”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即便是没有集体活动,“六一”这天各个群里也要互祝“节日快乐”,都说的不亦乐乎。有人说老年人是硬生生地把原本应属于儿童的节日给“偷”了过来,往自己身上安。我却不认为是硬生生地,我认为这是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是水到渠成的事。这说明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年人有了充分享受生活的条件,老年人的心情也开朗了。并且老年人的思想认识和生活理念也变的得开阔了、超前了。现在的老年人都认为:“只有身体好,才不会拖累儿女、拖累国家。有个好身体是对儿女最大最好的帮助。”
让我们与年轻人一起追梦新征程,赞赞新时代!
作者简介:
韩月莉,女,53岁。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人。自由职业,高中毕业,曾毕业于河北省蔚县西合营中学,高中毕业后曾在多个地方担任过代课教师,步入中年后,开幼儿园,几年后又外出打工。自幼语文成绩就比较好,直至现在也酷爱文学。
| |